至于对残雪及卡夫卡小说的评价,祁文认为他们的作品缺乏“情感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并认为:乏于情感就意味着难以深入人性的探求。文学主情,对这个看法当然认同。这里不做详述,在此简单说一点看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恰恰是走了一种反抒情的路子。其实,反抒情也是一种抒情,只是它有意避开了“易感”的浪漫主义情调而已。
整个时代情绪在发生大转变,20世纪的情绪是低暗的。在这根情绪之弦上,惊颤着奥斯维辛的血腥以及极权主义的野蛮行径,田园牧歌岂能复返?从眼前看,我们个人仅仅这三年多的经历,已对身心产生了什么影响,至少无法再唤出疫情前那样的状态了。
有人说,情绪不仅是各种意识的表现,而且是意识的储罐。人的各种身心体验也都向意识深处沉淀下去,又会从情绪的火山口释放出来。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呈现不同的情绪反应,但同样都触摸到了人性的奥秘。比如卡夫卡的小说,犹如深陷的梦魇,那是心灵在困境中的挣扎。梦是深沉的情感表达。我们能体验到由梦带来的感情震颤,甚至从梦中醒来时,余波仍在。
有关现代主义,有人把海德格尔、结构主义视为“反人道主义”的哲学;更有加塞特主张现代艺术的去人性化、去个性化。这些说法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因为我们还在沉浸之中。我们不愿打破“人本主义”的美梦,这个梦一旦破碎,日子确实很不好过。然而,这个梦确实是易碎品,人是“本”之不住的。若问,不立足于人,何以求存?问题正在于此。社会学强调个体的人无法脱离“关系”而独存;同理,整体的人也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要与各种外在力量取得平衡。承认并相信他者的存在,而不是只相信自己。宗教信仰在20世纪再度兴盛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关系危机”。假如说古人的信仰起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那么今人的信仰则起因于人与人的关系危机。后一种危机使人再度把眼光投向远处。
王起庆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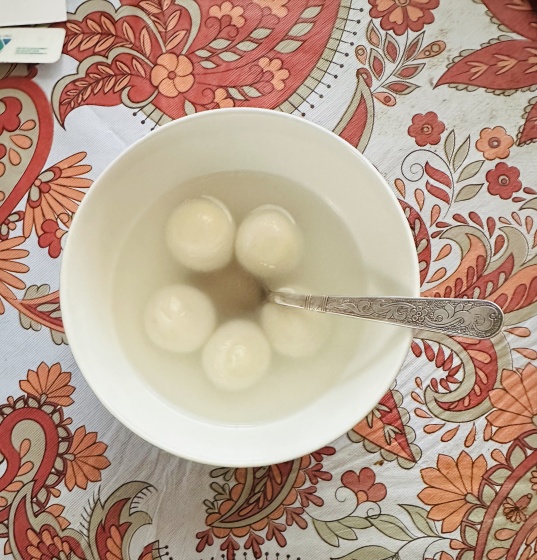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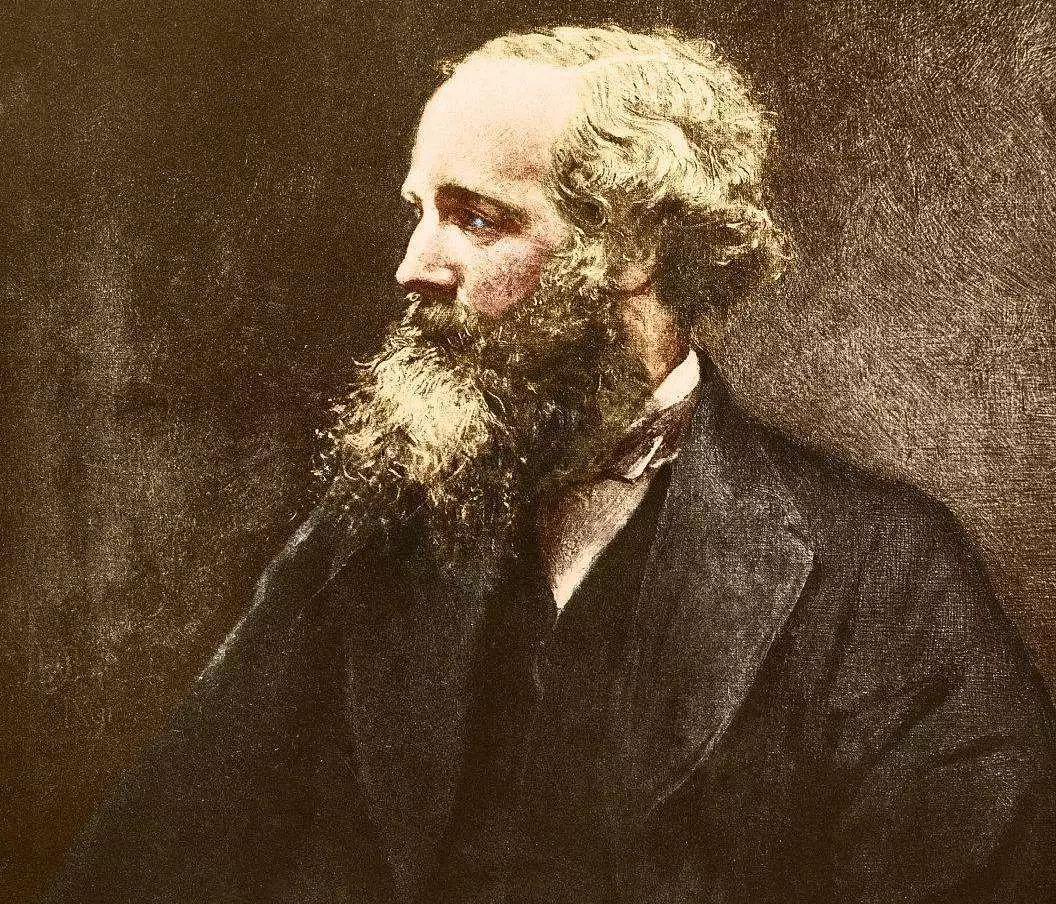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