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6岁离开生活的穷乡僻壤到城市读书的,从穷乡到省城,是“高中”后,从“低处”往“上”走的,等待我的可能是“锦绣前程”,可心底里依旧有一种远离家乡的恐慌和忐忑。而1966年的谭泽及其四千名城市青少年也在这样的年龄踏上西去的路途,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他们心里又有怎样的期待?那遥远高原的寒冷贫瘠,与他们出生城市的温润洋气形成的对比何止天壤之别!“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是年过古稀的作者在《兵团岁月》“写在前面的话”所用的词汇,这不是无病呻吟的修饰,而是一种刻在心版上,印在骨缝里,荡漾在脑海里的真切体验的写真。
在“飞奔格尔木”一篇中,作者开篇写道:“青海建设兵团驻地的前身是格尔木劳改农场。”这一行字占了一个段落,却让我浮想联翩。我想到了未曾开发的瘴厉之地海南岛,蛮荒无边的北大荒,甚至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这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都适合安置“犯人”。看看作者笔下的青海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青海陆续建起五十多个劳改农场,监管着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在押犯。农场所在地大都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交通闭塞,犯人即便逃亡,十有八九也得毙命在路上。”这样的地方怎么就成了城市学生的安置地了呢?“根本原因是青海省想引进人口发展农业,解决粮食缺口,为下一步的发展作准备;山东省想减轻大批城市失学青年带来的就业压力。”我读这些文字时,感到作者的压抑与克制,我觉得他一定有更深的思考,他没有行诸文字,却留下了让阅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在接下来的一段,又是一行平实无华的文字:“以上是去了格尔木以后慢慢知道和悟出的。”“慢慢知道”消磨的是青春年华,“悟出”了以后心里该产生多少冤屈和痛楚,这四千青(少)年从“东方瑞士”来到“劳改农场”不就是一种驱赶、贬谪和发配吗?凡是困难的时候都需要有人牺牲,这就是所谓“代价”,而谭泽们成为代价不是因为不优秀,他于1965年中考落榜,因为那个年月给他们的家庭出身盖上了特殊印记,“后来得知班上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基本都落榜了,而一些所谓出身好的,平时考试还有不及格的同学都被录取。这才知道落榜和成绩无关,和政治有关。”于是他们只好作为“代价”被牺牲掉了。青海正好需要劳力,青海的大片荒野需要兵团战士用汗水、血水浇灌,用肉身作犁去耕耘,甚至干脆用生命之躯作肥料,好让不毛和蛮荒成为“财富”之地,作者和这四千青岛学生便成了时代的实验品。现在想想岂不让人毛骨悚然?我的恐惧绝非无来由,如今城市青年失业率到底多少?这连国家统计局都不公布数字了,如此讳莫如深,让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事情成了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当年的青海、格尔木、劳改农场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怎不让人心生恐惧!
记得上大学时,读过一首激情澎拜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作者是贺敬之:“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此刻,……/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你可曾想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这首诗是那个年代的号角,鼓励着、呼召着、驱使着年轻人去往他们一无所知的那片荒凉境地,作者和四千青岛子弟一定也是受了这样的时代之声的激励,“那个年代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没有坐过火车。对外面的世界,大家既懵懂又向往。而对荒凉、艰苦这些词汇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没有真正的理解,更不知个中滋味,只知道艰苦和光荣是连在一起的。”时过多年,经历过沧桑的作者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西行的列车:“(1966年4月15日)专列下午四点出发,两点多钟青岛站就开始陆续涌来送行的人们。列车开动了,从青岛站到沙岭庄,沿途都是朝着火车挥手的市民。”作者心里清楚,“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不希望我去青海的,那么远,那么荒凉,在历史上那是流放地,解放后是安置重刑犯的地方。我们是按照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的比例搭配的,明摆着就是移民嘛。但是父亲当时对还不到十七岁的孩子并没有明说,只是问:不去不行吗?事后我想,面对政府轰轰烈烈的动员,他不能散布负面的言论。再说看到我连续两年报名,也不想打击我的热情。”这样的情景,我仿佛看到了杜甫《兵车行》的场面:“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可是,在那样的时代里,又有几个人能了解此一去意味着什么?即便是阅历丰富,洞察清晰的,又有几个敢透露半点疑惑,“出发的年轻人都挺自豪,市民也都觉得这是很光荣的。”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就是这样踏上了人生征途,来到了三千二百公里之遥两千八百米之高的格尔木,没有想到一去就是十八年。”十八年,在荒瘠中,从少年到中年,蹉跎了岁月,流失了青春,浪费了才华……
环境的严酷很快教会他们如何应对苦难,磨砺他们的意志。首先经历的是“高原行路难”:“……溪水把道路冲坏,汽车路过左摆右晃,有时摇摆幅度达到二三十度。每个人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路,……”;紧接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愫”就被高原龙卷风吹得四散,狂风裹挟着沙粒,“把那颗火热的心吹得哇凉哇凉地了”,“后来才知道,这叫沙尘暴,是格尔木地区最严重的气候灾害”;“栖身茅屋”睡大通铺,差点被坍塌的土墙活埋;春夏之交原本是莺飞草长的浪漫季节,在这里却要领教“蚊子的肆虐”。关于格尔木农场的蚊子,我曾听另一位兵团战士也是作者的战友张国柱说过,1998年我曾采访过张国柱,他回忆最生动的就是高原的蚊子,当时觉得有点夸张。在“恐怖的蚊子”一节中,张国柱的回忆得到了印证:“大白天站在野外身上落满蚊子,戴着手套一巴掌下去,打死的蚊子通常都有三四十只(此文在美篇发出后韩庚良战友跟帖说,他曾经一巴掌打死五十七只蚊子)。”最难堪的是出恭时,蚊子逮着这样的机会,更是狂轰乱炸,“根本就退不下裤子”,为了躲避蚊子侵扰,作者讲述了一个极端的“事件”:“我们班有个小哥有天实在憋不住了,就找了个铁锹头接着,蹲在宿舍里拉起来。班里人觉得太过分了,就去拽他。没想到他竟然低头抓了两手屎挥舞起来,把大家都吓退了。他就这样举着两手屎,一直到拉完”。经历过“缺水”“尴尬的供给制”……苦难一个接着一个。当时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身处其中的兵团战士或许已习以为常,但今天读到这些文字,我不由得心生恐惧,我从心底恐惧这一切,害怕这样的场景重复出现,重复让青年才俊白白浪费青春岁月!
艰难的生活仅仅是一种磨砺,熬过来,回头咀嚼一番,有时候还能咂摸出一点点“甜味”,可是有些人永远没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回味了,《兵团岁月》其中一节“老回之死”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这个故事转述的是王沛东的讲述,我和沛东兄曾经朝夕相处过一年余,他讲述过一些兵团经历,我能记住的有“埋枪”的故事,颇有黑色幽默元素,而关于“老回”则是一幕血淋淋的惨剧,作者在文章里记下的文字如下:
那一年开春,老回等七八个人去大坑里起沤的“肥料”往地里运。大坑没化冻,十字镐都刨不下去,他们就用雷管炸。那天埋下了十个雷管,点着导火索后大家就躲得远远地,等着炸开了好装车。
那时战友们正学着划拳。青海人喝酒都要划拳,一是为了热闹,二是青海到了冬春季蔬菜副食品缺乏,往往只有一小盘泡菜做下酒菜,唯有依赖划拳才能把四五斤白酒灌下肚。
……那时战友们初学此技,下地工间休息时常常聚到一起练习。就在等着雷管爆炸的空,几个人又划将起来。
这边吆三喝六,那边咚一咚一咚地放着炮。数到九响后,没有动静了——有一个哑炮。谁去排炮呢?大家说:划拳,谁输了谁去。
一番比划老回输了。他一边往大坑走,一边还不服气地嚷嚷着:我不服,回来再划!
就在老回走到大坑中间时,突然一声轰响,大家眼看着他被炸得离了地,一条胳膊飞起来。老回被炸死了。
大家非常难过,也很是后怕——若划拳输的不是老回,那就必定是他们中的某一个。老回是替他们死的。
……回到青岛后,私底下和战友、朋友、同事喝高兴了,偶尔也划上几拳。有人问,你们青海兵团的人怎么都划拳这么好?我就讲老回的故事,告诉他们这等“拳术”是以生命为代价练出来的啊。
一个活蹦乱跳的青年就这样失去了生命,为了什么呢?为了沤肥,当时农业学大寨,上面瞎指挥,要求积肥,而青海的冬季严寒,埋下的麦秆灌上水后,不仅不会腐烂,反倒成了坚实的冰坨,根本不具备积肥条件,可是即便积不成肥,也得瞎忙活,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兵团战士的生命!
另一个悲剧故事是“盲流和小丁”。在岗哨上冻成狗的故事的主人翁小丁为了向绰号为“盲流”的战友要一根烟,开玩笑地举起枪来,结果冻木了的手指无意按动了上了膛的枪,一个生命就此殒灭。“盲流”和小丁本来就是好朋友,前来处理后事的“盲流”的哥哥提出不要处理小丁了。但是小丁却提出必须要接受处罚,否则一生不得安宁。之后小丁被判刑四年。
如果说上述两幕悲剧是作为旁观者的客观记录,而“丧父之痛”则是作者自己在大悲之后压抑着悲情的文字描述,写作时的冷静,文字的朴素,情感的真挚都不能掩盖无尽的遗憾和痛楚,这是彻骨的痛,哪怕过去那么多年,依旧能从文字里面感觉得到那个黑暗时刻失去至亲的悲情。因为连长不愿意相信电报通知家人病危的真实,就断然拒绝他去打电报询问情况,等到父亲病故的消息传来,连指导员竟因他不请假外出打电报而给他队前警告处分。人性泯灭到这样的程度,真实匪夷所思。
“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还在颤抖,禁不住悲伤和气愤!”印象中的作者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写这篇回忆时已年逾古稀,他说出这句话自然可以想象内心得有多么悲愤,以至于那么多年过去,依旧没有消化干净。这篇回忆最后一段最为平实,却也最耐人寻味:“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后来得知父亲死于医疗事故。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父亲出身不好,人已经没了,家里没有追究,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何其无奈?这才是真正的实录,这才是一个人的历史。
这部《兵团岁月》唯一温暖的部分是关于友谊、爱情和生育的。其中感人的章节有“怀念志光”“男大当婚”“养儿育女”等,姜志光,经历过兵团岁月的企业家,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写的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跟沛东兄拍摄纪录片《青岛人》,当时经费紧张,沛东兄带我去青岛红星化工厂找战友姜志光化缘,我见到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的姜志光身穿工装,在车间里压根看不出他的身份,朴素得有点不真实。
后来“(姜)志光带人去贵州安顺办厂的时候,给地区有关部门打电话,希望和地区领导交谈一下。对方听说他们住在一个每人每天十元钱的小旅馆里,立即觉得这可能是一伙骗子——沿海城市大型国企的领导怎么可能不住大宾馆?领导带着疑虑去小旅馆见到志光一行,交谈后十分感动,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
办厂初期,锅炉试压的时候,志光三天三夜不离现场,困了就睡在锅炉旁的水泥地上,只铺了一个草垫子。有一年除夕,志光从青岛开完会赶回贵州和员工一起过年,给随他去贵州办厂的青岛员工带回两个大口袋,里面是青岛大馒头和甜晒鲅鱼,以解他们的思乡之愁。志光背井离乡在贵州、重庆等地大山里奋斗了二十多年,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也给集团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厂子上了市,他没有一分钱的股份。”
作者笔下的姜志光闪现的是高原之光,是兵团艰苦岁月锻造的钢铁汉子。他后来生病了,战友们为了满足他最后的愿望,与死神赛跑,不远数千里将弥留之际的姜志光从深圳接回青岛,细节生动,感人至深!通过这篇记述,我更加理解了兵团岁月战友情的珍贵胜过黄金!而爱情在任何环境里都是浪漫的,养儿育女在任何时候都是孕育希望,友情、爱情和亲情是艰难中的支撑,让兵团岁月不至于漆黑一团,而散射着细微的亮光。
经历了“悲欢离合”,当面对“难以为继”的局面时,兵团战士经过“抗争”,他们终于病退困退回山东。这不是叶落归根,而是大树移栽,他们曾经是青岛海边的黑松幼苗,后来被移栽到高原,长成了耐寒抗旱的胡杨树,如今再一次被移回,几番折腾,让他们的生命力更加顽强。回到青岛,兵团战友很多在不同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青海高原的风、格尔木的寒冷给他们的除了苦难还有力量,他们更多的是汲取了力量,而忽略了苦难。而对我这样一个读者,我却不能不更多地体味他们经历过的苦难,因此我恐惧这样的苦难。
因为自己在媒体工作,接触的人相对多一些,我有幸认识很多青海兵团战士和他们的子女。而对青海兵团战士的认识最早来自对王沛东老兄的印象,因为一部《青岛人》,和他朝夕相处一年有余,他吃苦能力,面对困难不萎缩不气馁的闯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韧劲,都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知道谭泽先生更早一些,我参加工作时,他已经是报社的领导,我的同学就在他手底下干活,因此也就知道了这位当时很年轻的媒体领导。凭我的印象,谭泽和王沛东是两种性格的人,但通过《兵团岁月》这部个人信史我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甚至觉得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或许在四千青海兵团战士身上都具备,这就是青海高原独有的环境、气候、人文、习俗十八年的陶冶、镌刻在他们身上的,有些甚至与他们的身心融为一体无法分割,就连他们的下一代也抱有青海高原的印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四千青岛青年如今都步入古稀,他们,连同他们的第二、第三代遍布青岛,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群体。从城市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兵团战士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丰富了青岛的城市文化,给社会带来一个很特别的群落,这部《兵团岁月》是一块沉甸甸的基石,正好填补了这一话题的空白,是值得重视和关注的。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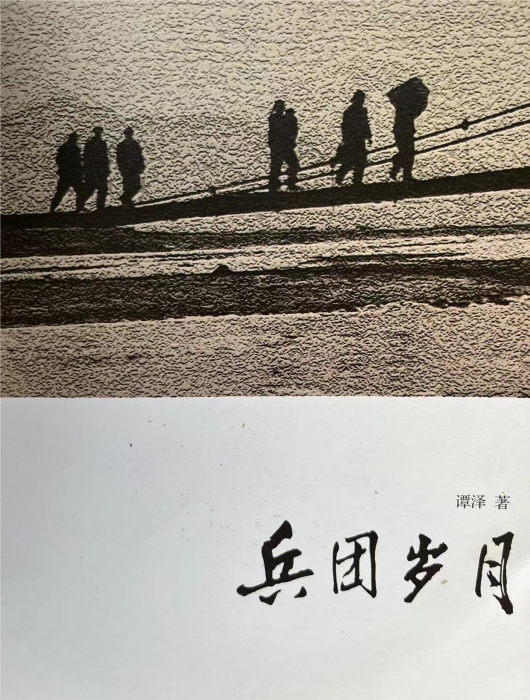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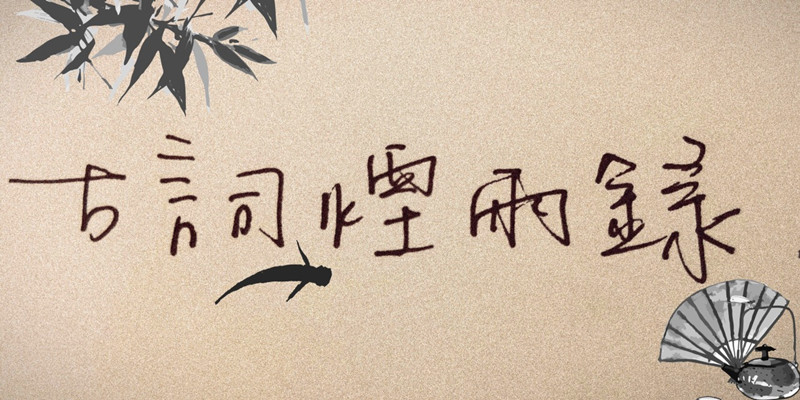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