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无望的岁月里,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我的爱人给予我的爱像太阳的光辉温暖了我的心,他伴我走出了人生的阴霾。当这段爱情最终结成婚姻的硕果,她又经历了严霜的考验,这朵爱情的花朵依旧那么新鲜、那么芬芳。
爱的萌芽
1969年1月17日清晨,寒冷没有风,晨曦中道路两侧的路灯还闪着昏黄的光,略显泛白的天际中有几颗亮着的星,似乎也冻得瑟瑟发抖。
青岛四中的门前,已经是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我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那个知青组,灰蒙蒙的人群中有一个人鹤立鸡群,排在最前面的一位高高的带着眼镜的男生,见我过来,问了我的姓名,热情地把我手中的网兜接过去,“来,我替你拿着,我们是一个组的。”
“哦,谢谢。”我的心里一热,偷偷地看了他一眼,自己长这么大,从来没和男生这么近距离地说过话。殊不知,洪锡的这一接,便接过了我的一生,命运把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此时的青岛火车站已是人山人海,欢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红色横幅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搅在一起。命运之神正开动着轰隆隆的列车把这些知青们送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洪锡是老三届中的老高中,我们知青组的组长,他戴着宽宽的黑边眼镜,虽然一副斯文的样子,可干起农活来一点儿也不比当地的农民差,往地里运肥,他小推车中的肥总是堆得高高的,很轻松地就走在了大家的前面。他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像一个大哥哥,他带领着我们知青组的同学们种的小白菜,红萝卜都长得绿油油、水灵灵的,赢得了老乡们的赞扬。我在心里偷偷的爱上了他,可那时年龄尚小,羞于开口,我把他记在了日记里。
下乡以后,我们和村里的农民一个待遇,干活挣工分,洪锡能干,他能挣最高分10分,而我只能挣7分。队里分给我们一块儿自留地,让我们自己种点儿小粮食补充不足。同学们分别从两个队里牵来两头牛,一头大黄牛和一头小黑牛,让它们帮着我们耕地。谁知那头小黑牛一见到那头大黄牛就往它的背上爬,我那时少不更事,见它们那样,便大惊失色,高声喊道:“快来人啊,它们打起来啦!”洪锡举着鞭子,不慌不忙地过来,一边驱赶着它们,一边说:“叫你们打仗!再叫你们打仗!”在旁边看热闹的老乡和同学们笑成一团,我愕然:笑什么?我问他们笑什么,结果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没人告诉我笑什么。
麦收季节到了,丰收的喜悦伴着炙热的阳光和有生以来从未经历的劳累,考验着知青这些年轻学生们的承受力。我随着生产队的社员们下田干活,稚嫩的手掌磨出了水泡,瘦弱的身体被累得生了好几次大病,我顽强地抗争着命运。
洪锡看我整天在地里干活实在可怜,麦收季节破例安排我在组里给知青们做饭。我的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感激,每每看到他下工回来,便赶快递给他一碗水,他接过碗,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
冬天又临到我做饭了,连绵不断的雪覆盖在柴草上潮乎乎的点不着火,急得我想哭,洪锡便帮着我把柴草从柴草垛中抽出一些晾在屋内。我们难得吃一次饺子,12个大青年正是吃饭的好年纪,大家一块儿帮我擀干饺子皮,洪锡把三个面剂子摞在一起,一次能擀三张饺子皮。看着他能干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幻想。
有一个阶段知青组里按饭票吃饭,分粗粮和细粮,我吃地瓜多了,胃就烧心的难受。一天,趁着伙房里没有别人,洪锡便把自己的细粮票换给我,低声对我说:“我就愿意吃地瓜,你小,多吃点细粮吧。”“我不要,你干活那么累。”“拿着!”他不由分说地把细粮票塞到我的手里,我低着头忍着眼里的泪珠不让它们掉下来,手里攥着他接过递过来的细粮票,心里喜忧参半。
春夏秋冬,知青和老乡们一起在黄土地上周而复始地从事着简单而原始的农活收入微薄。那时我拿着一毛钱往青岛的家中寄信,八分钱买个邮票,一分钱买个信封,余下的一分钱在小卖部买两个针留着缝补衣服。
几年过去了,随着形势的变化,知青组里的同学们,有在当地就业的,有被推荐上学的,有通过关系当兵的,知青的家长们使尽了浑身解数找关系托门子让自己的孩子走出这广阔天地,而我由于出身富家,这一切统统没有我的份。洪锡后来在学校里当老师,也第一批走出了农门,分配到了当地的粮食部门。
甜蜜的爱情
同学们都走了,另一个女生也病退回青岛了,原来热闹的知青组里只剩下了我一个女生。送走了他们,我关上门,看着冷冷清清的宿舍,一种从未有过的委屈、寂寞和无望袭上心头,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顺着我年轻的面颊流下来,最后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将来怎么办?难道真的在农村一辈子吗?我为自己的命运而哭。路过宿舍的农村女友们听见哭声,敲开房门,陪着我一起落泪。玉香搂着我说:“晚上我们来和你作伴吧。”
“不用,有这条小狗和我作伴就行了。”我流着泪哽咽地指着趴在自己脚前的小狗说,小狗站起来摇着尾巴,嘴里响着阵阵的应声。
听说组里又走了几位知青,只剩下了我自己,洪锡骑着自行车从几十里路外的粮管所赶了回来,还给我买了许多好吃的,不断地安慰我以后还有机会。
从此以后,洪锡隔三差五地来组里看望我,我那颗冰冷麻木的心慢慢地有了些温度,埋藏在心里许久的爱情之苗开始苏醒了,每逢洪锡到来,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愉悦,我信赖他,这是世上任何人都不能给我的一种生命的依靠,我有什么事情都请教他,他也愿意帮助我,这是心灵上的相融和默契。但是一个女孩子的矜持,还是使我羞于表达对他的爱意。
1972年临近春节,我要回祖籍探望家人。汽车凌晨5点半发车,我们下乡的地方距离汽车站近10公里,按说下半夜的3点就要出门,一个女孩子哪敢自己走夜路。于是我和洪锡说了,第二天下半夜的3点他准时地敲开了我的宿舍门,把包裹放在自行车的车把上,我看见车梁上绑着一根粗粗的铁棍,问他:“这个铁棍是干什么用的?”“防身用,万一碰着坏人,我用它来保护你。”洪锡一边整理着东西,一边说。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暖暖的,顺从地坐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洪锡带着我走出村庄,狗叫声渐渐远去。凌晨的田野里,四处漆黑一片空旷无垠。东北风无阻无挡地在田野中呼啸着,寒气逼人,高阔的天空中满挂着的星斗,它们眨巴着眼看着我们。洪锡弓着身子顶着风用劲地蹬着自行车,一路上还不忘回头和我说:“往里坐坐,我给你挡着风。”我不好意思靠近他,只是用两只手把住车座的边缘。
来年初春,毛毛细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黄土地,远处的田野里,老农扬鞭扶着犁耙正在春耕。洪锡冒雨来到我的身边,递给我一封信,接过信的一霎那,我从洪锡清澈明亮的眼睛里看见了快乐期盼的火花,我的心瞬间像有一头小鹿在砰砰地跳,我转过身去躲开他的注视。信中他向我表明了爱意,若是我同意他愿意和我共度今生。我的脸霎时羞的像新娘的红盖头,但谨慎、文雅和良知在呼唤着我,我矜持地把信还给他,说:“我出身不好,说不定会在农村待一辈子呢,不行,那会影响你一生,你会后悔的。”我那时心中早有一种悲壮的打算,若是三十岁我生日那天还跳不出农门,我就自杀生命就此了结。这个想法以前我也曾对洪锡说过,他当时脱口说道:“那你生日那天,我就守着你一天。”回想起这事儿,我说:“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不是,我是真的喜欢你。”“那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和我好。”我噘着嘴娇嗔地问道,“哎——”洪锡急了,“那时候你还小,是个小女孩,我不能欺负小女生吧。”我感觉到脸呼呼地好像发烧,低头不语,“答应我!”我的一只手忽然被他使劲地握着,洪锡的手是那样的有力、那样的炽热,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全身心如痴如醉的愉悦,也许这就是最真挚的爱情?
在我人生最难过的当儿,洪锡给予我的爱情光辉四射,把我包裹起来,我把眼前的困苦暂且忘掉了,那些日夜缠绕着我对前程的忧虑,都让甜蜜的爱情一扫而光。夜晚,我们手拉手,沿着茫茫的田野慢慢地缓缓而行,我把那青青的麦浪比为青岛大海日夜不停的波涛,把这田埂比为栈桥;有时我们坐在田野的边上仰望着满天的星斗,那些星星是那么的遥远,洪锡把木星和小熊星座指给我看,并把它们的故事讲给我听,多么不可思议啊,宇宙间竟有那么多奥妙!在那漆黑的夜晚,我们依偎在一起,望眼欲穿地期盼着下一次知青就业的消息。我早就和洪锡说过,不跳出农门我是绝对不结婚的。在那茫茫的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从上帝的安排,任凭命运之舟把我们载到遥不可知的远方。
洪锡等了我五年,五年后全国知青拔点,我才得以回城就业。在那艰苦难熬的岁月里,爱情的甜蜜压倒了生活的苦涩,是他的爱拉着我走出了人生中最为阴霾的时光。
婚姻交响曲
我们结婚时,洪锡已经30岁,那时就算是大龄青年了。他工资28.5元、我18元,我们一贫如洗,只是把两张单人床靠在了一起,供销社的一张黑色两抽桌被我用红纸覆盖着,上面罩着我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勾成的白色桌布,一张玻璃板压实了这拮据的幸福。我们两个下乡时从家里带来的木箱摞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我们的结婚誓言是:人有富贵我有手,双手得来幸福贵。
洪锡心灵手巧,没人教他怎么做木匠,可我们家的双人床、写字台、椅子、饭橱和大衣橱等等都是他利用下班时间一点点做出来的。
洪锡聪明能干、性格开朗,由于工作出色,36岁就被提拔为粮食局的副局长,业务能力在系统内是数得着的。那时是计划经济时期,粮食统筹统购。洪锡和公社书记及大队的生产干部一起到麦田里估产,以此计算出各个村庄应该上交的公粮。洪锡从麦田里摘下几只麦穗,放在手心里搓一搓,吹去麦皮,放在嘴里嚼嚼,围着麦田走一圈,就能估算出这块麦田的产量。只要洪锡说出的数,八九不离十准确率很高。
我们结婚那会儿全国经济紧张,连一般的生活用品也买不到。夏季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走了近80里路,回到曾经下乡过的大队,大队支书送给我满满的一筐土豆,又帮我绑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从供销社买了几条肥皂(当时肥皂按票供应)。在返回县城的途中,时近中午的天刷的一下子地黑了下来,要下雨了,我想:快骑!赶到下雨之前到家。我弓着腰飞快地蹬着车轮。那一瞬间的暴雨是突然降临的,“哗——”大雨一下子就从变黑了的天空中倾泻下来,我慌忙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打住车撑子。雷鸣夹着闪电,闪电带着雷鸣,大风和着暴雨狂泄而下,以致我都来不及从车座上取下雨衣,就被大雨鞭打着躲在自行车后面的筐子下方,一会儿风又转向了,大风夹带着暴雨又从另一个方向袭来,我立马转向车座的另一面躲避着如注的暴雨,透过被雨水浸过的眼镜片,朦胧中眼前是一片花白的水的世界,对面几米都看不清物体,公路上的汽车都停开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浑水滚滚,我忽然发现绑在车座后面的肥皂正在被雨水冲向水沟,这时我顾不得大雨浇灌,一手扶住车子,一手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点儿、一点儿斜着身子用手指去勾那即将滑向水沟的肥皂,这可是“走后门”买来的。
内陆的夏季极度炎热,气候变化多端,暴雨戛然而止,说停就停了,雷声滚滚远去,天空霎时晴朗阳光普照,公路两旁被暴雨洗过的庄稼显得格外翠绿,被淋湿了的树木无力地摇动着它们的叶子,我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落汤鸡,衣服被雨水淋得紧贴着皮肤,我捋了捋头发上的水,低头瞧着自己的这副狼狈相,怎么回去?这是条省级公路,平时车辆繁忙,刚才的大雨连过往的汽车都停运了,现在它们一辆接着一辆呼啸着从我身边驶过,不时地有人伸出头来看看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儿。我解开后车座上的筐子拿出雨衣,穿在身上,这样可以遮挡一下衣服紧贴着皮肤的窘相。
我推着自行车走进粮食局的大院,凡是碰见我的人,见我的头发湿漉漉地打着缕,雨衣却是干干的,无不惊讶关怀地问:“这么大的雨,你这是上哪儿啦?”听见声响,洪锡赶快从屋里出来,接过自行车,问我的第一句话却是:“地里的麦子怎么样了?”我心中的委屈和无名火,瞬间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你老婆死了,吃麦子去吧你!”这件事传出去以后,被局里的人当成笑话,流传至今。
不过在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丈夫一直迁让着我,从来没有和我计较过什么。有时候他下班后,高兴的时候,会把我抱起来高高地转一圈,我大叫:“晕—放下!”“真是不懂浪漫!”洪锡笑着把我放倒在床上讥笑着我。有时他也哼着天鹅湖的曲调:“叨叨叨,叨希拉……”模仿着猪八戒跳小天鹅湖的舞姿,双手提溜着自己的衣角,双脚踮起,头一歪,那笨拙夸张的舞姿,常常逗得我捧腹大笑。
可天有不测风云。洪锡工作起来常常忘了休息,有一天他突然剧烈头疼倒在了办公室里,经医生诊断,是脑干出血无法治愈。看着僵直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我感到自己的心被揉碎了,医生用了当时最好的药,为了减轻他的脑压,在洪锡的头顶上生生的凿了一个洞,一滴滴往外滴着的脑脊液中不时地带有血丝,他的气管被切开,“噗—”的一声,一股鲜血直喷到天花板上,最要命的是他的大脑必须冷冻,否则会坏死……
我日夜守候在病床前,看着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昏迷不醒的丈夫,心如刀绞,恍如隔世。我按时为他翻身、吸痰、冷敷。我趴在洪锡的脸边,用小剪刀一根根剪短还在生长的胡须,流着泪在他的耳边说:“你一定不要死,洪锡,我要你活,你听见了吗?”洪锡那时已经没有知觉了,却从眼角缓缓地流出了几滴泪……
14天后,洪锡终于醒过来了!上帝给我留下了丈夫沉重的身躯,带走了他的半个灵魂,病魔使他面目全非,大脑放弃了对半边身体的指挥权。十五年来,我每天要在床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脖颈,洪锡用右手搂住我的腿,在“一、二、三!”的号子声中,才能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地梛到床边,洪锡一米八的个头,二百斤的体重,给我的体会就是一个字“沉”,扶着他一步步挪到沙发上坐下,然后给他刷牙、洗脸、喂饭。为了促使他的大脑恢复功能,我经常给他读司马迁的《史记》,洪锡也会用含糊不清的话语提示我念了错别字,我们的笑声飘出窗外,令邻居们不解。洪锡虽然丧失了身体的部分功能,但他能用心体会到我对他的爱,丈夫虽然不似常人,但我依然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
张爱玲说过:隔了三十年的时光,再好的月光也未免有些凄凉。夜深人静时,我陪丈夫边回忆曾经的艰辛与幸福,边看着一弯月牙从这幢楼顶移到那幢楼顶,月光虽然凄凉却依然美好!
有人说: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而老年人结伴走向死亡,才真正是相依为命。
时光如梭,白驹过隙。当前尘往事在我脑海中一一涌现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在时光长河流逝的瞬间,已经走过了如此漫长的人生旅程,回首过往,我的生命竟然如此的多彩斑斓,每一块堆积的碎片中都记载着丈夫在世时我们的幸福,同时我也痛苦地体会到:无论幸福和苦难都会成为过去,想抓都抓不住,如同沙漏。
本文在“第二届‘中国知青作家杯’征文评选”中荣获纪实文学类一等奖。
宋慧珠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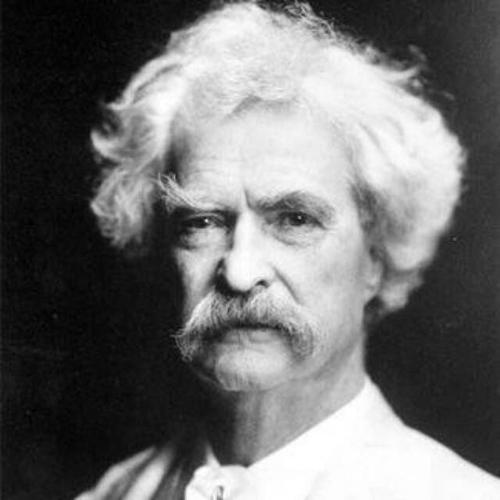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