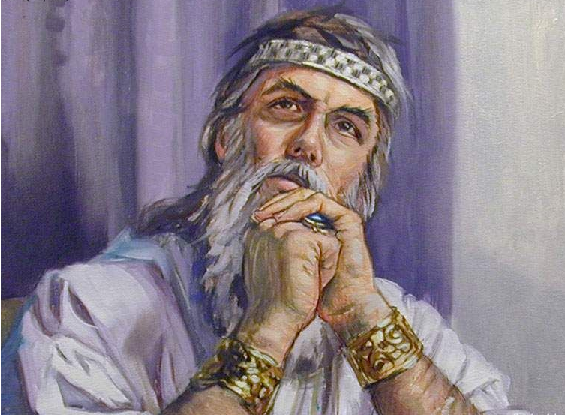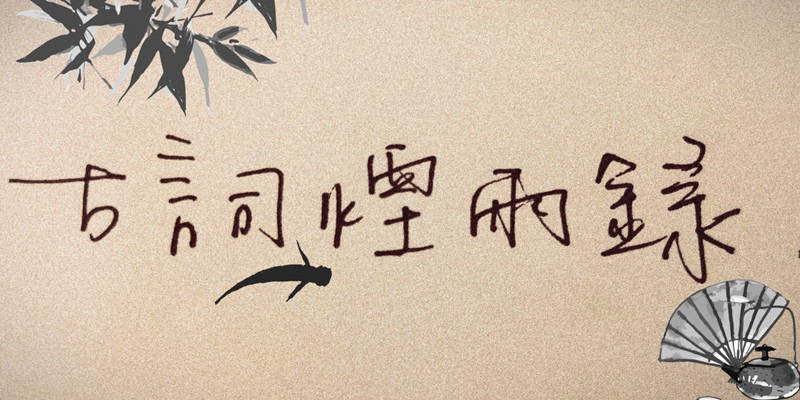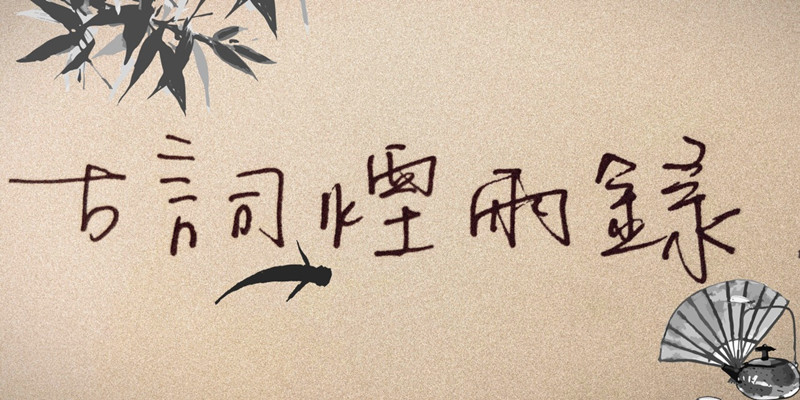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 “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章惇在信中劝勉苏轼“痛自追悔往咎”,并相信“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除了精神上的抚慰,章惇还送药和钱财给他,就章惇当时的身份而言,不失真诚,反倒是苏轼用语过于谦卑,不能不看出苏轼对刚刚升迁的章惇有些许的提防。苏轼描写自己追悔闭门的处境,在一阕《卜算子》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诗人苏轼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他坚守的信念始终如一,那就是以诗劝谏,匡扶明君,于世有补。这不仅是苏轼的信念,“诗经”以来的士之传统就是如此,有操守的士人无不以此作为持身立命的根本。苏轼通判杭州之前,神宗曾亲口对他说:“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之过,指陈可也。”正是这样的信念和期许,才使得苏轼不顾亲友规劝,将看到的新法弊端屡屡行之诗文。哪怕经历牢狱之灾,其心中仍持有不可动摇的根底。乌台诗案发生之际,退休的张方平上书皇帝试图营救苏轼,就说道:“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者无以罪,闻之者足以戒。”贬谪中的苏轼给好友李常信中,可以见出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於邑,则与不学道者,不大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心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仆虽怀坎坷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他对章惇的“诚恳”检讨,可谓惭愧至极,而对李常的口气则是傲骨凛凛,气势如虹,这应该是他的真实告白。两封信,写给不同的人,前恭后踞,给章惇的信固然有感念老友劝慰之情的成分,更多的是对时局的恐惧。经过牢狱,尽管保住一条性命,但政敌对他却依旧虎视眈眈,他怕稍有不慎再陷囹圄,他不能不心怀恐惧:
示谕《燕子楼记》。某于公契义如此,岂复有所惜。况得托附老兄与此胜境,岂非不肖之幸。但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虽托云向前所作,好事者岂论前后。即异日稍出灾厄,不甚为人所憎,当为公作耳。千万哀察。
从以上材料分析,他对章惇的回应,作秀的成分也就不言而喻了。另有一件事,很值得关注,这就是苏轼写信向章惇求助,让章惇帮忙释放他在徐州任 上答应释放的犯人一事。书略曰:
……轼在徐州日,闻沂州丞县界有贼何九郎者,谋欲劫利国监,又有阚温、秦平者,皆猾贼,往来沂、兖间。欲使人缉捕,无可使者。闻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胆。其弟岳,坐与李逢往还,配桂州牢城。棐虽小人,而笃于兄弟,常欲为岳洗雪而无由。窃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门户垢污,茍有成绩,当为奏乞放免其弟。棐愿尽力,因出帖付与。不逾月,轼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两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轼语棐:“但尽力,不可以轼去而废也。茍有所获,当速以相报,不以远近所在,仍为奏乞如前约也。”是岁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见报,云:“已告捕获妖贼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状申告捕妖贼事,如棐言不谬。轼方欲为具始末奏陈,棐所以尽力者,为其弟也,乞勘会其弟岳所犯,如只是与李逢往还,本不与其谋者,乞赐放免,以劝有功。草具未上,而轼就逮赴诏狱。遂不果发。
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见报,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实,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录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于轼者,凡为其弟以曩言见望也,轼固不可以复有言矣。然独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发,犹能奋身不顾,以遂其言。而轼乃以罪废之故,不为一言以负其初心,独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绝人者也。徐、沂间人,鸷勇如棐、岳类甚众。若不收拾驱使令捕贼,即作贼耳。谓宜因事劝奖,使皆歆艳捕告之利,惩创为盗之祸,庶几少变其俗。今棐必在京师参班,公可自以意召问其始末,特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与一名目牙校、镇将之类,付京东监司驱使缉捕,其才用当复过于棐也。此事至微末,公执政大臣,岂复治此。但棐于轼,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轼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于朝廷,又不一言于公,是终不言矣。以此愧于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独愿秘其事,毋使轼重得罪也。
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国监去州七十里,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三十六冶器械所产,而兵卫微寡,不幸有猾贼十许人,一呼其间,吏兵皆弃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啸召无赖乌合之众,可一日得也。轼在郡时,常令三十六冶,每户点集冶夫数十人,持却刃枪,每月两衙于知监之庭,以示有备而已。此地盖常为京东豪猾之所拟,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辄复及之。秋冷,伏冀为国自重。
这件事,他没有交给旧党盟友,而是交给了章惇,一来是当时章惇正大权在握,借助他的权力事半功倍,另外也有故意显示二人亲密无间的意味。
在黄州住了些日子,苏轼从惊恐中满血复活,活泼、幽默、机智重新呈现,他和章惇二人的友谊愈加亲密,通信不再小心翼翼,而恢复了戏谑的笔调,苏轼《与章子厚二首》向其倾诉了自己与苏辙如何过贫困的生活和节俭的方法,甚至妻子治好家里的病牛等琐事也成为通信的内容。苏轼在黄州有诗:“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笑我何所求。吾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惇就笑他诗句先步行后驾车,“何其上下纷纷也”,苏轼辩解自己是以腿脚为车轮,以神思为马。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二人的交情如初,几乎没受诗案影响。可惜,这样的友谊没能维持太久,接下来的政治变局让二人重新陷入扯不断理还乱的党争中,终于彻底反目。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