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哲学家对自己生活的社会如此乐观。卡尔·波普尔自诩为“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1986年他在自传的后记里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我的这一信念惟有变得更为强烈。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
这种乐观主义的形成缘于卡尔·波普尔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了纳粹和苏联帝国的兴起与覆灭。1992年,距他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还有两年的时间,他在自传的第二版的后记中说,也许我活得太久了,所有的近亲都已经去世,最好的朋友也去世了,甚至最好的学生也都离去。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苏联帝国的解体,他说:“除了几乎毁灭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希望的历史事件”他呼吁“让我们放弃左右的极化,这种极化部分是历史决定论的遗产。”
当我在1980年代第一次读到卡尔·波普尔的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的时候,立即被他扉页上的一段话击中了:“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难者。”
历史决定论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声称能带来一个更加平等更加正义的社会。而支撑这一信念的据说是基于知识的进步,基于一种历史规律。但是卡尔·波普尔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掌握这种“知识”,假如有这种“知识”的话。
在其著作《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卡尔·波普尔总结了自己的史学逻辑:
(一)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的。
(二)我们无法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预言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三)因此,我们无法预言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四)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相应于理论物理学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五)因此,历史主义方法的基本目标就是构思错误的,历史主义就是不能成立的。
除此之外,波普尔还发现了历史决定论者难以置信的智力狂妄。“狂妄地称自己为这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使得为了一种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教条,或为了一种结果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不惜冒他人生命的危险成为义务,这是可怕的事情。”更加可怕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不加思索就接受了这样一些教条,这对于能够阅读和思考的人来说特别糟糕。知识分子天然的优势在于批判性,在波普尔看来,一切科学或社会理论都是假说性质的,只有经过批判的检验才能稍许接近真理,我们的知识是在不断地试验中排除错误而成长的。“理性”和“理智”的最好意义就是对批判开放:准备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
历史主义者声称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了加速他们所称的历史意义或者目的,就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进而对人类也要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在纳粹德国这类“改造”是为了造就金发碧眼勇敢坚毅的“新人类”。
与卡尔·波普尔同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直观性”。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控制和重建我们的社会,“国家权力必定增大,直到国家几乎等同于社会为主”。集中权力是容易的,但是集中每个人心灵里的知识则是不可能的,然而要维持庞大的社会按照统治者的愿望所进行的有计划的运转,这种“集中”就是必要的。要知道每个人心灵里的秘密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不得不以消除个人的差异的办法简化这个问题,最后就不得不以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浇铸人们的兴趣和信仰。
历史主义为什么能够吸引和诱惑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呢?一部分原因是它表达了人们心底里对世界的失望,这个世界并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理想和完善梦想,转而要寻求我们的“黄金时代”和“理想国”。古希腊人认为人类是从黄金时代演变而来的,而赫拉克利特是第一个发现变化观念的哲学家,“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人类的流变只会越来越糟的,道德越来越败坏,人就应该回到他的黄金时代。
历史主义也即历史决定论源远流长。卡尔.波普尔在其后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发现了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条线索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黑格尔,一直贯穿至今。
卡尔·波普尔的成名之作《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就像一对同卵双胞胎,他们都脱胎于早期的著作《研究的逻辑》,《研究的逻辑》可以看作是科学发现的哲学,但是到了《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则发展成为历史哲学或者政治哲学。他在一开始就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定无疑的?”这些在知识的逻辑上看似不自觉的观点,对我们看待自己和政治的态度上往往是决定性的。
“开放的社会”代表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它的敌人就是二十世纪暴行的策源地,在这部巨著中,波普尔把笔墨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等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每个男人都是战争机器,每个女人都生育工厂,至于儿童,“必须骑在马背上观看真实的战争;如果能够安全,还要把他们带到战场参加战斗,让他们尝尝血腥的味道”。总之灌输仇恨、斗争是把青年训练成专业的武士阶级必要的组成部分。一位现代作家把当代极权主义教育描绘成“一种紧张而持续的动员”,真是一语中的。
1919年,卡尔·波普尔发现了历史主义的悖论,他还发现了一个使人陷入某种境地并且越陷越深的机制。正如卡尔·波普尔本人,深感历史主义漏洞百出,但是却克制自己指出这种悖论。这一现象部分是出自对于社会主义者朋友的忠诚,部分是基于对“事业”的忠诚,还有就是有一个使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的理智和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就会陷入这个机制。他希望通过确信那个“事业”本质上是善的来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他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越道德和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次理智和道德的牺牲,一个人就会越陷越深。
这一点很像一个赌徒。每一次筹码的牺牲必须由更大的筹码捞回来,每一次投资的失败都试图用进一步更大的投资赚回,直到输得精光为止。也许直到有一天被关进了自己人建造的监狱,革命者才会幡然醒悟,但是极权的大网已经织成,悔之晚矣。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推而广之,革命者最大的悲剧就是建造了关押自己的制度牢笼。(节选)
原载 葛陂小记
原标题是《第一次读到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时,立即被他扉页上的一段话击中了》
张祚臣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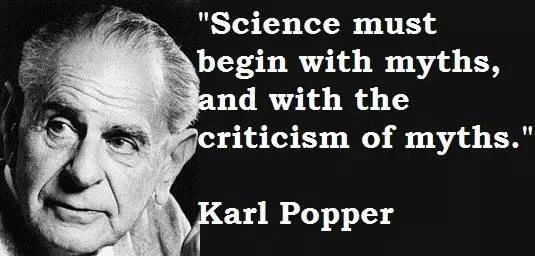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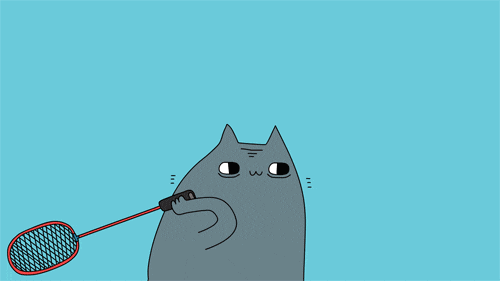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