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近读唐圭璋先生编《全金元词》,原因在于几乎所有文学史对金元都有所忽视,但拿“词”之一体而言,所有选本对金元词作所选不多,以至于在印象中,词的词汇、语境、意象几乎都是江南的,而偌大一个北中国仿佛付之阙如,鉴于此,我希望在金元两朝词人词作中读到我熟悉的场景和意象。当读到元好问时,发现,他与山东颇有渊源,早年随从父居掖县(今莱州),晚年被拘聊城,不免生出些许亲切感。元好问的文学创作成就,在文学史上可以比肩唐宋一流大家。元好问今存词377首,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清代刘熙载评论:“金元遗山……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
关于元好问
元好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世称遗山先生。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元好问自称是唐朝诗人元结的后裔,父亲元德明隐居不仕,以诗文著称于世。元好问出生七个月后,就被过继给叔父元格。五岁时跟随叔父住掖县(今山东莱州)。七岁能诗,被称为神童。从二十岁起,“下太行、渡大河”,开始了各处游历的“觅官”生涯,参加过数次科举,但并没有得到好的成绩。二十八岁时赴汴京以诗文谒见当时的礼部尚书赵秉文。赵秉文对其诗作大为赏识,“以为近代无此作也”,对其大加奖掖,遂名震京师。然而由于仕途偃蹇,元好问二十八岁后的诗作一改早先的朝气蓬勃,满篇宏大抱负的路数,流露出对科举不顺的厌烦、懊恼和灰心。写出诸如“一寸名扬心已灰,十年长路梦初回”(《示崔雷社诸人》)、“无端学术与时背,如瞽失相徒怅怅”(《雪后招邻舍王赞子相饮》)的诗句,低迷与无奈的情愫不时地流露于诗中。
天兴元年(1232),元好问升至尚书省左司都事,却遭遇多事之秋。这年三月蒙古军围困汴京,恰逢他的三女儿早夭。五月,赏识提携他的赵秉文逝世。十二月蒙古军第二次围城时,金哀宗率兵弃城逃离。而汴京城内粮食已绝,米价暴涨,百姓多有饿死,已经发展到食尸甚至食人的地步。转过年的1233年正月,守城西面元帅崔立以汴京城投降蒙古军,自封郑王。蒙古军占领汴京后,崔立自认为救活了京城百万民众,曾要求元好问等文人为其立碑颂德。元好问等文臣内心视崔立为叛贼,不愿落笔,另一方面又恐为崔立所害,于是找到未有官职的文士刘祁来撰碑文。之后元好问又向耶律楚材上书,举荐一批知名文士,请求后者予以保护。此两件事令元好问被质疑有“气节”问题,这种质疑一直困扰着他。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秋,元好问被元政权长期拘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天兴三年(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金朝覆亡后,元好问陷于崔立功德碑之事的悔恨自责中,由此招来的毁谤更令他积郁难排,常常沉醉酒中以求解脱。这种情绪下他创作了代表了思想和艺术的最高成就的“丧乱诗”。
五十岁时,元好问回到故乡忻州。回到故乡后,以极大毅力编写亡金野史,在故乡筑起“野史亭”,以彰著史之志。同时,编有《东坡乐府集选》《唐诗鼓吹》,致力于保存金朝文化。他还在封龙山与张德辉、李冶一道讲学,学生众多,并称为“龙山三老”。六十三岁时,元好问与张德辉北上觐见忽必烈,说服忽必烈接纳尊信儒学,并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促使忽必烈任用儒士治国。元宪宗七年九月初四日(1257年10月12日),卒于获鹿(在今河北省)。
《摸鱼儿·雁丘词》写作时间及意图
元好问十六岁时往并州赴试,途中遇到一个捕雁的人对他说,今天捕到一只大雁,另一只脱网。但脱网之雁悲鸣不去,最终撞地而死。元好问听后买下这两只雁,将其葬于汾水边,并有感写下《雁丘词》。其中首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至今仍脍炙人口。原词及序抄录如下:
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号曰“雁丘”。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此词上片写雁,情境俱化。“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一个“问”字破空而来,为殉情者发问 ,实际也是对殉情者的赞美。“直教生死相许”则是对“情是何物”的震撼人心的回答。古人认为 ,情至极处,“生者不以死,死者不以生”。“生死相许”是对至情至爱的盛赞,这“直教”二字,则声如巨雷 ,惊天地,泣鬼神。“天南地北”二句写雁的生活 。“双飞客”即为雁 。大雁秋南下而春北归,双飞双宿,形影不离,经寒冬,历酷暑,多像人间的那一对痴男怨女 。无论是团聚 ,还是离别都仿佛眼前,刻骨铭心。“君应”四句揣想雁的心情。“君”指殉情的雁。侥幸脱网后,想未来之路万里千山,层云暮雪 ,形孤影单,再无爱侣同趣共苦,生有何乐呢?不如共赴黄泉吧,这里对殉情雁的心理世界做了形象的描写,读来备感哀痛沉滞。
对这首词的下阕过片三句,缪钺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双雁是葬在汾水之上,于是联想到当年汉武帝泛舟汾河时所作的《秋风辞》。”又谓横汾、箫鼓皆用《秋风辞》中的语典:“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他指出,《秋风辞》中有“草木黄落兮雁南归”之句,可以暗扣住主题的“雁”字(见《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招魂楚些何嗟及”二句,谓汾水之上,一派凄清,欲待歌《招魂》之曲,返其魂魄,已来不及了,只有山鬼在风雨中为其哀啼。“何嗟及”出自《诗经·王风·中谷有蓷》:“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意思是有一女子为丈夫抛弃,啜泣不已,悲叹莫及。《招魂》《山鬼》皆屈原所作之楚辞,《招魂》中多以“些”为句末语气词,其声至悲,故后世称凄厉之音曰“楚些”。《山鬼》中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之句。这几句是词人想象,被词人细心埋葬的双雁,不会与莺燕同归黄土,而会被千古骚人,狂歌载酒,常来凭吊。双雁死后的哀荣,连上天都要嫉妒的。
下阕过片三句,由“雁”跳越到汉武故事,显得很是突兀,缪越先生的解释,也略嫌牵强,如以为因雁丘在汾上而联及汉武,则词中应有交代,因此读至此,觉得整首词截然形成两段,不成一体,觉得前面关于多情“雁”的铺垫与后面生发出的慨叹,有一点疏离之感。这一情况宋人已有发现,张炎便说“断了曲意”(张炎《词源》)。难道,汾上这一处小小的雁丘能承载得起如此深重的哀伤吗?这就涉及到对这首词如何解读了。一般认为这首词紧紧围绕“情”字,以雁拟人,谱写的是一曲凄恻动人的恋情悲歌,表达对殉情者的哀思,对至情至爱的讴歌。果真这是一首单纯的情诗(词)吗?其实不然,或者说它所表达的“情”并不单纯。何以见得?这就需要从考订其写作时间入手。可以肯定的是,以《摸鱼儿》行世的《雁丘词》并非是元好问十六岁赴试途中所作,而是后来修改的,这在其词序说得很明白。那现在所见到的《摸鱼儿·雁丘词》作于何时呢?前述中我们知道,金亡后,元好问于封龙山与张德辉、李冶一道讲学,而这首词有李治同题和词,可以确定,此词应作于元好问五十岁以后,即金哀宗殉国,金朝灭亡后。李治(字仁卿)的和词如下:
雁双双、正飞汾水,回头生死殊路。天长地久相思债,何似眼前俱去。摧劲羽。倘万一、幽冥却有重逢处。诗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风嘹月唳,并付一丘土。
仍为汝。小草幽兰丽句。声声字字酸楚。拍江秋影今何在,宰木欲迷堤树。霜魂苦。算犹胜、王嫱有冢贞娘墓。凭谁说与。叹鸟道长空,龙艘古渡,马耳泪如雨。
此词主旨在写元遗山营雁丘事。上片“诗翁感遇”四句,由写雁转到写遗山葬雁,过片三句,是说元好问不止营雁丘,且创作了芳馨悱恻的清词丽句,字字凄楚。“小草”是稍稍起草。“拍江秋影”谓雁影,宰木是坟墓前的树木。李治在他的词中感叹双雁既逝,魂魄飘荡霜天之中,固然凄苦,但总算比汉代远嫁匈奴的王昭君,唐代至死仍为妓女的贞娘(应为真娘)要自由,雁丘的人文意义,在朔漠黄沙里的昭君青冢,虎丘山下的真娘墓之上。“鸟道长空”用杜甫《秋兴八首》句意:“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意指故都难返。“龙艘”字面上指汉武帝横中流而济汾水的龙船。马耳用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语典:“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问题又来了,大雁殉情,纵令人感动,又何至于“马耳泪如雨”?与“鸟道长空,龙艘古渡”又有何关系?
结合两首词的意境,走进元、李二人的历史空间,不能不让人深思,雁丘词真的只是写情之作吗?有没有隐藏着一些别样的寄托呢?
据《金史·哀宗纪》载,金哀宗于天兴三年(1234)正月戊申,传位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诏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危难之际,完颜承麟唯有答允继位。次日,承麟受诏即皇帝位,即金末帝。正月十一日,正在行礼,蔡州城南已经立起宋军旗帜,诸大臣亟出抗敌。宋军攻破南门,蒙军攻破西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四面杀声震天。金军将士顽强抵抗,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殉国。金哀宗自缢于幽兰轩,享年三十七岁。临死之际,自评道:“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脱脱的《元史》认为:哀宗“在《礼》‘国君死社稷’,哀宗无愧焉。”历史对这位亡国之君评价还是颇为公允的。完颜承麟闻知金哀宗死讯,率群臣入哭,认为:“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就,实是可哀。”谥曰哀宗,哭奠未毕,外城被攻破,退保子城,同日,完颜承麟也死于乱军中。金哀宗、金末帝并死社稷,皆不独生,内侍完颜绛山收哀宗骨葬于汝水。这让元好问想起自己十六岁时听闻的双雁故事,以及当日所营的雁丘。他重理旧作,想要在词中寄托其对哀宗、末帝的无限同情,这才有词的下阕“横汾路”三句对汉武帝的联想,也才有招魂之些、山鬼之啼。这样,这首词的情感逻辑就顺理成章了。尽管元好问词中无一字涉及哀宗殒命的“幽兰轩”,李治的和词却有“小草幽兰丽句”之语,其中“幽兰”是否指向哀帝殒命处?如是,则可以循此理解,元、李何以要拿雁丘拟于人的冢墓,又何以为“鸟道长空,龙艘古渡”而叹,因为雁丘实指代哀宗在汝上的坟茔。另,遗山集中,有古乐府《幽兰》一首,历来被视为吊哀宗之作:
仙人来从舜九疑。辛夷为车桂作旗。
疏麻导前杜若随。披猖芙蓉散江蓠。
南山之阳草木腓。涧岗重复人迹希。
苍崖出泉悬素霓。翛然独立风吹衣。
问何为来有所期。岁云暮矣胡不归。
钧天帝居清且夷。瑶林玉树生光辉。
自弃中野谁当知。霰雪惨惨清入肌。
寸根如山不可移。双麋不返夷叔饥。
饮芳食菲尚庶几。西山高高空蕨薇。
露槃无人荐湘累。山鬼切切云间悲。
空山月出夜景微。时有彩凤来双栖。
据此可以认为元好问将年少时所作《雁丘辞》改订为《雁丘词》,不只是为了叶宫商,而是别具一种怀抱。这首历来被目为爱情词的《摸鱼儿》,不是一首单纯的爱情颂歌,而是元遗山作为亡金遗民感慨兴亡、心系故国的血泪之唱,是亡国之呻,是哀绝之吟。
这首词尚有杨果(字正卿)的和作,题云《同遗山赋雁丘》:
怅年年、雁飞汾水,秋风依旧兰渚。网罗惊破双栖梦,孤影乱翻波素。还碎羽。算古往今来,只有相思苦。朝朝暮暮。想塞北风沙,江南烟月,争忍自来去。
埋恨处。依约并门路。一丘寂寞寒雨。世间多少风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说与。还却怕、有情多被无情误。一杯会举。待细读悲歌,满倾清泪,为尔酹黄土。
杨正卿后来仕元,位至参知政事。词中“想塞北风沙,江南烟月,争忍自来去”等句,不正是故国之思语吗?末云“一杯会举。待细读悲歌,满倾清泪,为尔酹黄土”,他应该是读出了遗山词背后的亡国遗民心迹和哀痛之感。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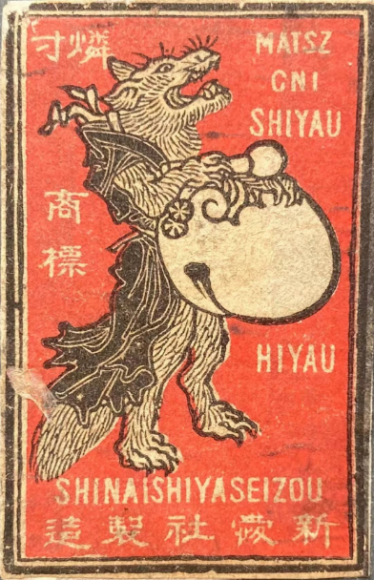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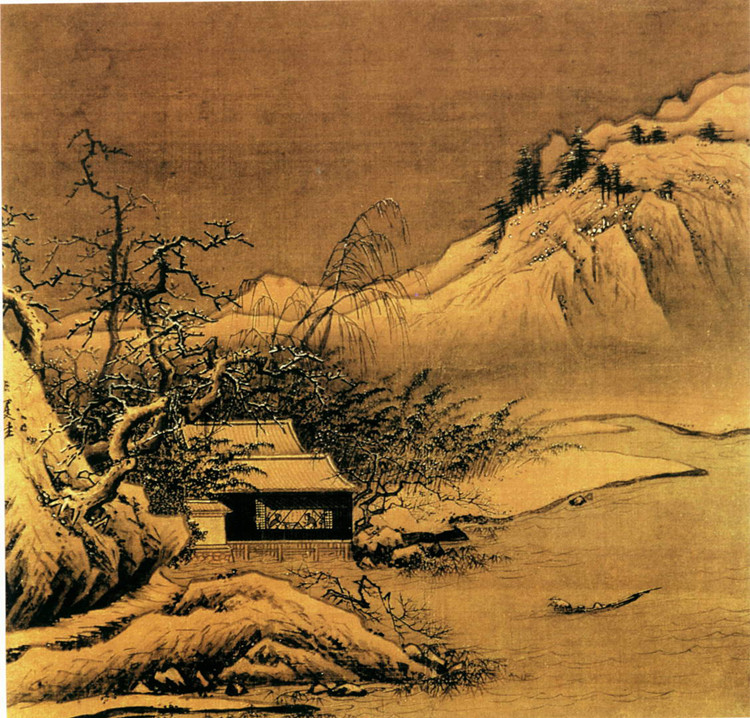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