酵化的眼光
人的眼光是被酵化了的,其至因是爱意或敌意。《创世记》载,禁果结在伊甸园分辨善恶之树上。始祖偷吃禁果后,就开始分辨了。善,含有善美、完美之意,从人的意欲出发,就是对效果满意;恶,含有缺乏、矢不中的之意,从人的意欲出发,就是对效果不满意。人去分辨善恶,并非说分辨之下那个被分辨的东西就真是善的了,或者真是恶的了。人哪有这么精确的分辨力?除非是神。为此,“分辨”这个工作可算是人的某种僭越。
有说“爱憎分明”的,却很难说“善恶分明”。前者是主观态度,后者是道德状况。因此,这二者会出现错位,即:所爱者并非善,所憎者并非恶。何以如此?因为支持爱憎的动机主要是人的意欲和自我意志。即便是善恶分明了,爱憎也不一定按常理对位。比如,当下的“世界态度”可叫做“选边站”,而网络媒体已显示:有很多人站到恐怖主义那边去了。
说道酵化的眼光,真是一种令人感慨的现实。在一个阴鸷的人那里,酵化的眼光含有毒素,但愿笨拙而单纯的人不要被这种眼光灼伤。在一个单纯而有爱心的人那里,但愿她没有觉察,就那么爱着,沉浸在不太真实的幸福中。
情景化的世界
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贝尔对莱布尼茨的评价很高,他说:“能在灵明世界里有益地、稳妥地旅行的人,无过于他了。”又说:“笛卡尔派认定一切心灵与身体的联合只有一个一般的规律,莱布尼茨却不是那样,他主张上帝给予每个精神一个特殊的规律,看来由此可以推出:每一个精神的原始结构都是与别的精神不同'属'的。”
最令人惊讶的事情莫过于观看人与人的差别,而这事其实本不该惊讶,因为个体差异的原始结构本来就有其不同的来源,人又走着不同的道路,最终成为彼此的异象。
在结构里、在经验里、在命运里,人能有多少自由?显然,都不如灵明世界所能够带来的那么多,虽然,这个灵明世界不能不牵线于结构、经验、命运,甚至环境。
环境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灵明是我们出游的世界,二者不仅衔接,而且可以交融。交融就是有爱的情景化的世界。
没意思
“没意思”比“无意义”更可怕,更毁灭。无意义尚可硬去追求意义,而没意思则很难再唤出意思了。深和浅有什么意思?善与恶有什么意思?如果不爱了,尚可悲悯,但悲悯又有什么意思?不得不说,“没意思”是一种天生的早熟、天性的死寂。“没意思”在其本性上带有死亡的气息。但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它还是一种天生的残忍,是对生命的残忍和否定。对于那种“有意思”的人,他们的爱好、追求、好奇、快乐,在一个“没意思”的人那里就不存在。如果问,实用主义者难道没有生命活力吗?他们为什么很少有好奇心呢?回答是他们也有活力,但他们的活力是关乎自己的,而不是对象化的好奇之心。
不可知论
历史上的重要哲学家绝大多数是不可知论者,他们是诚实和谦卑的求知者,基督教神学的基本精神也是这样。马主义则是坚定的可知论者,他们自认为什么都知道,因此什么也敢干,即所谓“大无畏”精神。我们注意到平庸现象,平庸者多数是可知论者。平庸是一种能够把腐朽事物迅速集中起来的能力,诸如机械唯物论、官本位思想、小市民的价值标准、精神产品的物质化、信仰观念的低俗化和实用化等等,这些好像正是为平庸者准备的饕餮之宴。
王起庆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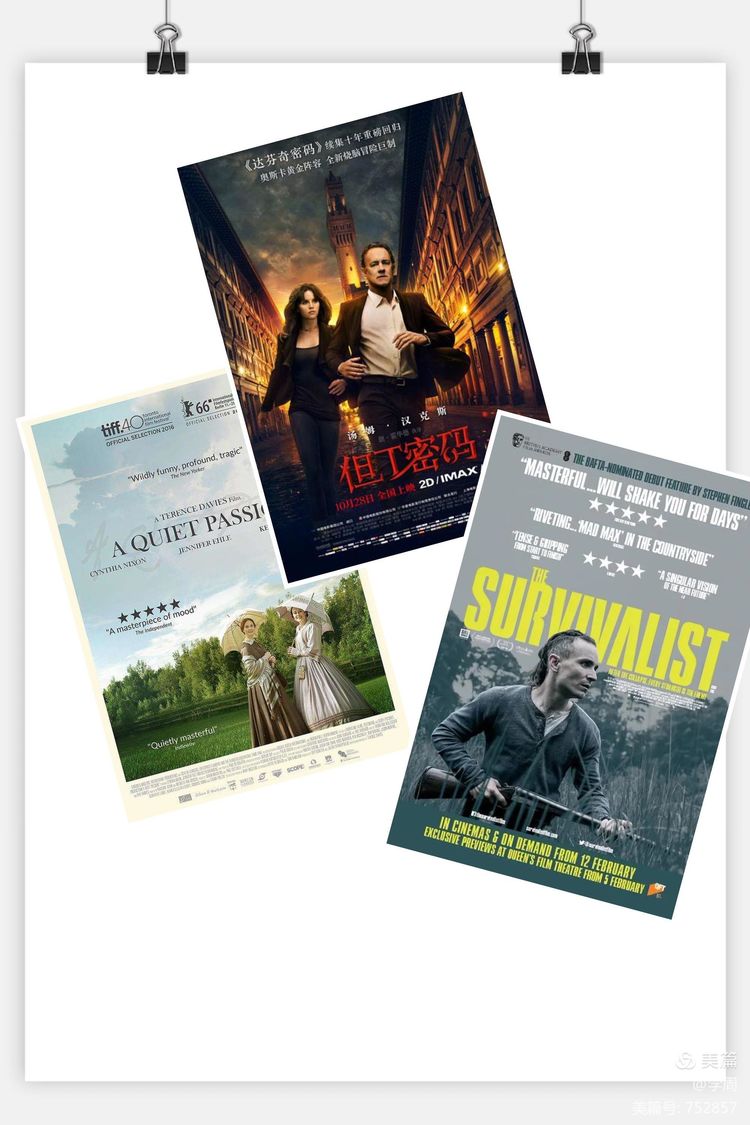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