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九月一号那天,牛老汉终于带着儿子牛小宝,当然也带着我们——百元钞票五兄弟上路了。几个月来我们天天被压在枕芯里,今天终于得以出来(虽然仍是被牛老汉小心翼翼地揣在衣兜里),心中和牛老汉一样畅快无比。很快,牛老汉父子俩乘上了开往县城的公交车。在拥挤的车上颠簸了近三个来钟头,牛老汉正准备下车时,发觉车门前面有点堵,然后仿佛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五兄弟同时感觉有谁用两个手指以飞快的速度从牛老汉衣兜里把我们夹了出来。糟了!我们被小偷扒去了!
待到牛老汉发现失窃并呼天抢地地高喊时,小偷已早溜进了一条无人的小巷子里不见了。小偷麻利地把信封撕开,不屑一顾地丢在地上,然后喜笑颜开地把我们几兄弟点了点,就放进他的上衣口袋里了!我们气得咬牙切齿,就因为这个可恶小偷,害我们成了肮脏之财了!而我们就这样与牛老汉失去了联系。
小偷悠然自得地吹着口哨,立马拐进了一家商店,抽出我们兄弟其中一位买了一包香烟燃上。到了第三天,我们兄弟五人就分散剩两位了;第四天傍晚,小偷揣着我们剩下的两兄弟和几名新来的兄弟来到了一家赌场——他们和我们一样来路不明!这个赌场真是热闹喧天,到处充满了狂叫、谩骂声。看小偷欢快的神情,这几日他在公交车上是屡屡得手了,我们都希冀他在赌场上输个精光,也好解我们的心头之恨。说来也活该小偷倒霉,他输得一塌糊涂,赢家是一个脸上长了雀斑的大胖子。大胖子把我们抓在手上,眼睛笑得缝都看不见了。
这新换的主也不是个好东西,第二天大早我在牛老汉家的唯一的兄弟就被他不知怎么花出去了,而这天晚上他便带着我和其他新的同伴来到了一家华灯闪烁的夜总会。他吃了又唱,一个人闹腾嫌不够,叫上两名浓妆艳抹的坐台小姐,然后唱了又喝,喝了再唱,最后我被大胖子塞进了一名坐台小姐的乳罩里。
坐台小姐揣着我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她的住所。我打量她的住所,家徒四壁,和她上班的地方简直判若天渊。她睡到第二天晌午才起床。起床后那个不施粉黛的她和昨晚那个浓妆艳抹的她,起床后神情凝重的她和昨晚那个浮声浪笑的她竟也判若两人。
在她住所没呆上两天的功夫,我就被她消费到了一家开餐馆的老板那里。过了些日子,我和几名兄弟被那开餐馆的老板当做薪水下发给了帮他打工的其中一个干瘦的伙计。
“老板,好像……少发了一百元五十元……”这名伙计将我们数了数,犹豫了半天,终于怯生生地说。显然,他挺怕这老板。
“我少发了吗?你上个月不是有天没上班吗?”
“是……可我向您请了假的……”
“你那叫请假?你那叫旷工!请假起码要提前一天,而且要写书面报告,懂不?你口头上请假就请假?”
“我爹得了急性阑尾炎,我也是突然知道消息的。电话里跟您说过……”
“好了,不要再解释了!每个人都跟你这样家里有这事那事的,那我这餐馆要不要开下去了?”老板打断他的话。
干瘦的伙计只好不再说话,默默地把我们放进他的裤兜里。下了班,他忙带着我们去了附近一家银行存了起来。
过了一段日子,我辗转到了一位包工头那里。这天,我听到那四方脸的老板娘跟那圆圆脑袋的包工头说:“我们让阿福给他班主任送点人事,让他把阿福的座位调到牛小宝的前面去不就得了。”我听到“牛小宝”三个字,不由得感到奇怪。只听他们的对话仍在继续:“恐怕不行,阿福那班主任平常挺严肃的,怕是不吃我们这套啊。”那板娘冷笑一声道:“教育局长就是我二舅,连校长都要礼让三分,再说,我们还给他好处,他一小小班主任连这点人情都敢不讲吗?”于是,阿福的那位包工头老爸带着我和几名弟兄来到了阿福班主任的家。在阿福的班主任一阵推让之后,我最终被阿福他爸“强行”塞进了阿福班主任的口袋里。
跟着这位班主任,我来到了阿福班的教室里。啊,牛小宝真的也在这里!真想象不出那天把我们弄丢后他和牛老汉怎么过来的!牛小宝本来座位排在阿福的前面,却因为我的作用,被阿福占到前排去了!唉,我帮不上牛小宝的忙,却反而给他添乱了!难怪人们都说钱不是好东西,可那些将钱使坏的人们知道我原本多么地委屈和无辜吗?
后来的岁月里,我频频地更换新主,经过各色各样人的手:他们之中有做投机生意的商人,也有“不许百姓点灯”的官人,有囊中羞涩的学生,也有一贫如洗的乞丐,他们面孔不一,性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我敬畏有加。少了我,他们做什么都不方便。谁会跟我过意不去呢?
有一天,我辗转到了一位年轻人的手里。这个年轻人面孔很熟悉,我仔细一看,他不就是牛小宝吗?原来经过了多年生活的艰辛,牛小宝已熬完了中学又念完了大学,终于领到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了!
牛小宝买了大堆礼品兴冲冲地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家。牛老汉从那幢愈发显得低矮的瓦房里奔了出来迎接儿子。这些年来,牛老汉似乎更苍老了,但精神却比从前更矍铄了。牛小宝把我从衣兜里掏出来,郑重地交到牛老汉微微颤抖的手上时,牛老汉的一滴浊泪从眼睛里流了出来,将我给洇湿了。
2007.1.31
何美鸿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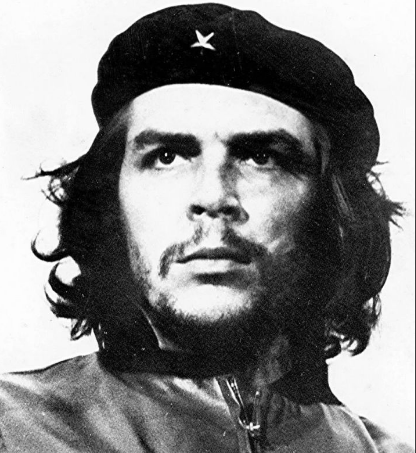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