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女性容易引人注目还是其他原因,李娟的散文非常火,集子印量也很大。我倒觉得很多好散文,反而被埋没了,例如朱苏进的《天圆地方》,围棋与人生,棋盘与社会,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与围棋的设子布局一样缜密,而且细节充沛。文章发表好多年了,一直没引起注意。
这样的例子很多,读者愚昧,被宣传或刻意制造的舆论引导,人云亦云,稀里糊涂,你指望他们能有什么品味?
▲小时候看书,是真正的看书,甚至有吃的作用,化为肌肉骨血。现在看书确实是“看”,看完就完了,有时候看到后面忘了前面。一个人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吸收率最高。莫言童年时看的书,奠定了他讲故事的扎实基础。
▲“吃”贾平凹。
我在西北大学读硕士班的时候,有一次和班上的同学穆涛、刘浏等人一块去贾平凹家,贾平凹在西北大学有个套二的房子,是他作为中文系教授的福利待遇,据说贾很少来这里住,他在文联还有房子。这天晚上穆涛带我们去贾平凹那里玩,拉呱时穆涛说到社会上所谓研究贾平凹的,出书,搞讲座,都在忙活挣钱,那些人挣大发了。言语里颇多不服。“贾主编,你能不能让我们也吃你两口?给点信息,我们也写点赚点?”
贾那几年刚发表《废都》,作品影响很大,又写了《霓裳》,如日中天。穆涛是贾平凹办的杂志《美文》的副主编,他说这些话既有吹捧抬举贾领导的意思,还有亲昵关系要赏钱的撒娇味道。
贾平凹眯缝着眼,笑眯眯地说,就让人家挣几个嘛,咱们急什么,有的是可写的,他们写的都是边边角角。
贾平凹是个金矿,淘金者和蹭热度的确实不少,可是说“吃”贾平凹,这词用的新鲜生动。想到一批人围着贾平凹啃,我忍不住笑起来。中国语言,真他妈的有趣。
▲夸张在文学里的应用。
莫言《一斗阁笔记》,里面马与老虎的搏斗,明显是违背动物学里的规律,一匹家里养的马,怎么能与山里老虎较劲?而且斗了好几个夜晚?莫言就敢在作品里展现,而且活灵活现。
他显示介绍这匹不同寻常的马,如何有个性,再出现马如何前蹄后蹄与老虎搏斗,甚至把老虎的一嘴牙踢掉,“老虎在吧嗒吧嗒掉眼泪”,让人如临其境。这就是描写的魅力。
还有他的《卖白菜》,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在哭,面前是退回来的白菜,那棵白菜是他们一家辛辛苦苦种出来舍不得吃的白菜,指望能卖几个钱,结果莫言被挑剔尖刻的老太太激怒,多算了一毛钱,惨遭退货,母亲哭着说,孩子,你让你妈丢了脸。
这些情节,没有夸张或文学情节需要,会是现实中发生的吗?但莫言让它发生了,而且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在这些故事走动的时候,莫言非常聪明地铺垫了一些细节,对那棵白菜的栽培,全家人过年包饺子或者换钱的渴望,戴护耳老人看破加钱的尖厉一撇,莫言都给读者交代了,故事的真实性得以延续。
▲浙江温州一个叫哲贵的作家,小说写得不错,内容主要是私营老板的心态和故事,我在一些杂志看了他不少作品,感觉哲贵有灵气,我还把他列入了“国内才气横溢作家”之一(自己弄着玩)。
谁知道咱看走了眼,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灵气过分大,还是现代作家都如此,哲贵刚写的长篇纪实文学《金乡》,使我大失所望。他在前言里说不受任何权贵影响,只是实事求是地写金乡,还要求当地宣传部长不准干涉,也不看稿,一切随哲贵作家的艺术表现需要。当地领导答应了。
于是无所顾忌的哲贵写开了,在《十月》杂志发表的长篇纪实,我期望值非常高,开头还行,毕竟还有气宇轩昂的前言。我看了开头一点,忍耐着看到最后,我一个老纪实作者,可以开诚布公地说,哲贵言行不一,偷懒耍滑,整篇《金乡》基本上是罗列一些报道材料,除了前边还有点创业者个性故事,后面百分之八十糊弄,该呈献人物内心复杂状态的时候,或者是说该展开文学描写的地方,他一笔带过,要不然就是含糊其辞,给读者的信息量极小。
特别是到了最后,哲贵直接把一些人物简介和企业材料剪贴复制,味同嚼蜡也不管了,典型的“行活”做派。
▲人的下意识,恍惚间,没发生的各种动作,故事发展,应该说文学广阔的领域。你实际不敢干的,在脑海里完全可以发生,那些痛快,淋漓尽致,都在虚幻的想象中。特别是受了委屈,你的仇人,或者你能制服的,在你噼里啪啦的拳脚里,铺展出故事。
然而你一睁眼,全是想象,梦一般虚幻。
类似的大脑臆想,其实莫拉维亚在写梦的小说里,做过很多实验,他的各种梦,包括梦中梦,展示人的潜意识和超意识,与幻觉异曲同工,变形的环境里,人性更加赤裸。
▲有一阵我热衷于练书法,临的帖子里有一本是鲁迅的诗,格律,古体,韵律严格。我在灯下写着写着,心里悚然一惊:先生诗里意象太沉重了!死,逝,长夜,淄衣,鬼,刀丛……这些字经常会跳出来,在你的心脏里扎一根钉子,疼痛,压抑,充溢着黑色的血,沉闷,还流淌着愤怒。
我没有专门研读这些诗,只是在运笔临字的时候偶尔碰到,可是从字面上洇开的灰暗,让人沉重。
先生对现实社会没有背过脸去,“横眉冷对千夫指”“怒向刀丛觅小诗”,他眼里的世界,哪里有半点歌舞升平!批判,唤醒,改造,真的是匕首和投枪。
我曾参加过书画家的笔会,写书法的笔下基本上是花好月圆,吉祥安康,厚德载物之类,一些书画家还带着小本子,上面是常见的格言诗词。如果我把鲁迅的诗奉上,“风雨如磐”或者“我以我血荐轩辕”之类,恐怕会不合时宜。
▲星罗棋布,这个成语的纠结一直在我脑海里。原因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上工代表的一番话。
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毛主席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占领一切领域,我们学校也和所有学校一样,从工厂来的车间工人成了学校的最高领导。那天,工代表在语文课上走到我身后,我真吓了一跳,好在那个工代表非常和蔼,他指着我语文课本上的一行字,问我:“听说你语文不错,作文写得好,我考你一下,这个‘星罗棋布’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慌神,急急忙忙思索了一阵,看前后文的意思,好像是很多,我赶忙回答:“是乱七八糟的意思。”
工代表点头,说非常好,到底是语文尖子。
哪知道,后来我从事新闻,多次用到“乱”的表述,“星罗棋布”被同事耻笑,开始我还不服,后来一查字典和成语词典,怎么会是“乱”呢?像星星一样罗列,棋子一样分布,只有多和美的意思,我中学的所谓“童子功”,是自以为是胡猜乱想,至高无上的工人阶级,又恰恰给了我表扬鼓励,这不是误人子弟嘛!
一次次见到“星罗棋布”,我一次次面红耳赤,那个年代的事儿,到底该怨谁?
▲说话,或者字词,习惯与环境,差别很大。
例如鸡蛋、鸡卵,意思一样,可我们习惯说“吃个鸡蛋”,若你说“吃个鸡卵”,也许旁边的人会窃笑,甚至骂你神经病。
割开一个西瓜,青岛人说是“嘎”,拿刀切嘛。西北人习惯说“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西安住了两年,当地人开口闭口“杀”,开始我很不适应,感觉冷森森的,“杀”这个字词有些恐怖。咱把“杀 ”用在凶猛或稍大的动物身上,植物水果类,那么圆润美丽,何必小题大做?
地区差,风俗习惯,风情特色。
我老觉得“杀”气势汹汹,与刀下美好事物相悖,不如吃、切之类温柔。特别是“杀了那个蛋糕”,青岛人怎么听怎么别扭。
其实人家说“杀”习惯了,也许觉得别的词汇不一定准确,甚至有些假惺惺。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咱不研究中国方言俗语,没有系统整理归纳。作家在表现人物和环境的地域差别方面,如果不注意说话,也许会让人贻笑大方。
▲潘向黎的文字,太老实,四平八稳,缺少敢作敢为的灵动。这一期《收获》发的她的几篇散文,就是题目打动了我,《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里面翻来覆去引的杜诗,赠卫八处士的白话解释,啰里啰嗦。
其实叙述不怕粗糙甚至毛边,灵性带来个性。四平八稳的散文太多太多,烂熟的文字烂熟的思维,全是套路,看了一堆还是茫然。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写自己最熟悉最拿手的,随着个性张扬,缤纷的世界在世界里展开,我们也是写自己的贡献者,组成美丽画面的一块颜色。不然,重复和堆砌,人云亦云,车轱辘,什么时候是个头?
▲人的天赋难得,要珍惜,维护和发展壮大,莫言就是例子。他本来好不容易到了部队,终于提了干部,一般情况下是走政工干部的路子,但莫言排除万难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发挥了他写作编故事的特长,后来名闻天下,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其实对写作有童子功的青少年真不少,他们的起点比莫言要高,但一般情况下,家长给孩子的要求,比孩子自然渴望的差得太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望子成龙,拔苗助长,各种文化补习课,各种特长班学习,谁受得了?
真不如莫言稀里糊涂左冲右撞,也许残酷的环境,歪打正着,可能正好使莫言成功。
文学,本来就是弹性非常大的需要灵性支撑的旁门左道,流行的话叫“不疯魔不成活”,的确,没有邪法子真不一定行。
▲写作,千万不要直线思维,人物和故事到了难以发展的一步,完全可以让其中的人物认错,整个故事走向马上变化,又回来衍生出许多可能。
其实认错非常正常,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认错给了我们发展情节的无限空间,看你的能力了。
▲写作的技术,有些是从灵气和才气自然喷发的,如果生硬的学习运用,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整体的协调和味道,差远了。
你可以想象,发自内心的笑容,与培训的露几颗牙齿,哪能同日而语。
我在一些孩子的作文里,经常发现令人惊讶的语句,那些想法来自孩子无所顾忌的童心,尽管这些孩子在一般的语文老师眼里,可能会“不守规矩”,在一路上无数次的考试摧残里会吃亏,你把他“修理”成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小大人”,获取了高分,他们的心灵也残废了。
毫无疑问,咱们的应试教育,灌输的强大力量,摧枯拉朽,修剪成千篇一律规格,即便有什么技术,也是死记硬背,与那些从心里流淌的,与表达自然而然的技术,相去甚远。
▲写作也有“医生”?当然有,病人太多,病症太复杂,诊断、治疗,业务繁忙。
有的病情一目了然,简单如感冒,语法或错别字而已,手到病除,三下五除二,嘁里喀嚓,容光焕发。
有的人沉疴在身或病入膏肓,如文章结构和逻辑混乱,无立意没细节,动大手术也难起死回生,真不如顺其自然,虽说是人命关天,可遇到此类文字,尽可能放弃,自生自灭比换脑袋剁腿卸胳膊要强。
大部分病人症状可断,只要对症下药,或手术,或住院治疗,修修补补即可痊愈。尽管有的需要慢慢调理,底子好,精气神在,好办。
▲抽象和具象的结合带来诗意。但这种结合不是拼凑,更不是故弄虚玄,而是有机的、内在的和谐统一。
诗意是自然而然的,诗人情绪和理智的喷发,有着极大的冲击力。
北岛的“滑进瞳孔的一盏盏路灯,滚出来,并不是星星”,还有“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女诗人路也:“我没有百宝箱,只有这把桃花心木梳子,梳理闲愁和微微的偏头疼。” 还是《江心洲》:“我这只北方的青虫,已经一头栽进了你这棵南方的菜心里。”
捧起悲伤,走进回忆,甚至癫狂在癫狂里,名词动用或软硬交配虚实相间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这也是诗歌表达美学的特征吧。
▲其实写作很简单,一句话,准确自然。仔细想想,能做到做好也不容易。 准确,得有多么丰厚的储备才能挑选;自然,不做作,心理足够放松强大才能收放自如,或者叫气韵生动。
▲美国作家罗斯的小说,非常精准地把握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别是他所熟悉的文化精英,诗人作家,大学教授,在性与爱、灵与肉间的犹疑搏斗,具体的家庭,婚外恋,一系列的矛盾和挣扎,入木三分,针砭肌里,我看得常常是一身冷汗。
其实人性就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复杂而单纯,你也许看不到天使,也看不到恶魔,但其中活生生的故事,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推到你面前,你会为他们哀伤,流泪,惋惜,愤恨,无间距的共鸣。
作家要制造噱头,夸张离奇的情节,那是技术,手艺的一二三,经过学习训练完全可以达到。盛开在大多数杂志的小说故事,无数蜜蜂追逐,与血淋淋的人性深处,距离多远?那一片喷上香水的塑料假花,在我看来,有着令人恶心的鲜艳。
罗斯注重的是内在的东西,人隐秘游走的灵魂,他剖析的是整个人类的病灶,不一定醍醐灌顶,但一定会让你心有所思,有所触动。
优秀的作家,生孩子的,做模特儿聚乙烯玩具的,天壤之别,一般读者难以区别,也是灵魂和技术的差别。
▲钱钟书对与读者见面,向来不感兴趣,他的一句话成为经典:“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我觉得不一定,作家和作品,特别是写出某一部出彩的,他一定有甘苦和体会,包括具体的组织和表述技术,对读者和同行有着参考借鉴意义。
当面交流,表情手势乃至语气,都比单纯的文字有感染力,印象也深刻。
即便是一只母鸡,如果会说话,也可以说说不一样的食谱,为什么味道不错,恐怕有其它母鸡另类之处。
比喻的特点虽然形象,但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锋利而失之偏激。
写于2019.12.
原载《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二期
轻博客转发4/1/2020 9:00:07 PM
杜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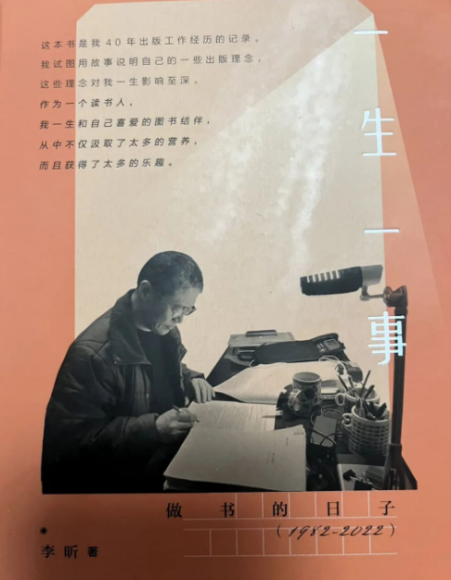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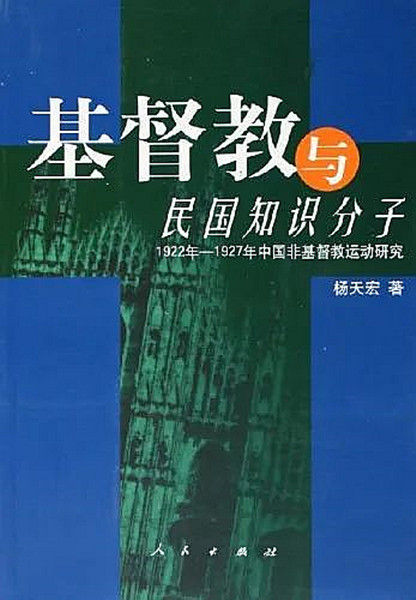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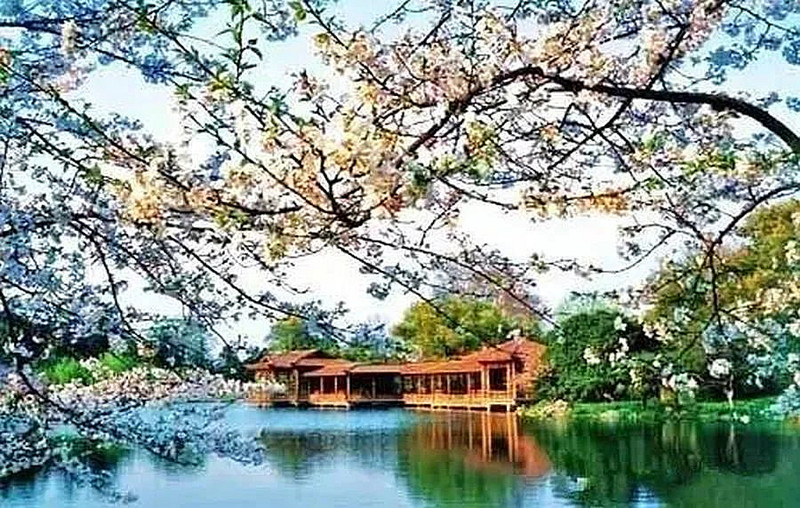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