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景里的语言是苍白的,耳朵也只是摆设,人们恨不能五官都变作眼睛,充分饱览四下里的风景。周遭满目是人们各种的姿势和造型,满耳是人们的喧嚣声和手机、相机的“咔嚓”声,然后千篇一律地以这些山地作背景的张张笑靥被摄下,留作日后“我曾来过这里”的纪念。
折腾半天,我们终于上了大巴,然后边看着车在蜿蜒盘曲的山路上奔驰,边看着夕阳转瞬便隐匿到了那其中一座山峰的后面。夕阳的余晖为山峰染上一道金黄的边,但迅疾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连绵不断的山峰迅速后退,又是连绵不断的山峰迎面而来。山上那些叫不出名的蓊郁的树,那竖起的高高的电塔,那高高的电塔之间长长的缆线,抑或那驻扎在山顶上的孤单的哨所,目之所及的所有物象,都在我们隔着玻璃窗的视线里一掠而过。我以为夕阳早已西下,不承想它竟在一道山谷间露出了半个脸,捉迷藏似的再次将一束柔光投向我们的车窗来。但旋即,这最后的柔光便被毗邻的山峰给完全遮没了。
我忽然便想起孩时,常常站在老家门前一节报废的拖拉机车厢上,朝着远如天际的依稀群山凝神眺望的情景。那淡淡的远山于我便是一种向往。孩时祖母告诉给我的许多神话故事里都与山有关。很多年我都一直痴迷于祖母讲述给我的那个名叫红桃的孩子的故事:那是一个秘密——有一座山,在红桃途经时每次都忽然将嘴张开,然后红桃便跳进那山里去玩耍。那山里有无穷无尽令人目不暇接的宝藏珍玩,红桃总是因贪玩屡屡忘了回家。那是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孩时很多年我一直都在猜想,那被人察觉了秘密跳进山里的红桃在山合上嘴之后什么时候能再出来。
逐渐长大后,虽然那个影响了孩时很多年的神话在无声息里被摧毁,减淡了神秘性的远山于我而言依然是一种魅惑。在我心里,山是永远充满灵性。山威严,高大,包容,静默。在我看来,那些依稀的远山,早早被赋予了一种完美人性的气度与品格。
一直想要寻找那样一种氛围,和萦绕梦中多年的远山做一次近距离的对话。一直期望着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与那被我赋予眼睛,赋予唇,赋予我生命中某种要与之碰撞的思维的远山,做一次灵魂深处的沟通。
但这样只带眼睛走过场般的团队旅行是不可能做到的。当我终于走进大山,却发觉那被众人目光瓜分的充满嘈杂和喧嚣的景物,让我感觉到的只有心的倦累。
天色渐渐暗下来,山色变得迷离而空濛。大巴依然在盘曲的山路上疾驰,一座又一座连绵不断的山峰依旧在迅速地后退。置身其间,我才陡然发现,这些大山于我原本依旧是那样地陌生。这一瞥而过的群山,有哪一座,能牢牢锁住我的视线?又有哪一座,能在我心里被久久记住?我所能记住的,也只有如浮光掠影般的关于山的空泛概念罢了。原来,山的某种特质,只适宜避开人群远远地眺望。
我的思绪在这盘曲的山路里乱飞。我想起曾有个人告诉我说,好怕一个人走进山里,怕迷失在山里再也出不来。——我曾为这话悸动,但我想此刻的自己,其实并没有走进山里。
天完全暗淡下来,近距离的群山终于只能看得见黑魆魆的轮廓。夜空里一颗亮晶晶的星星高高地悬着,相随我们的车很远,终于被一座突兀的山峰后遮没。车内亮起了灯光,我看见车窗的玻璃上映照出自己疲倦而落寞的脸庞。
刊载于《青岛财经日报》“红礁石”副刊
2024年6月26日 A8版 (见报时有改动,见谅)
组稿 / 编辑:周晓方
何美鸿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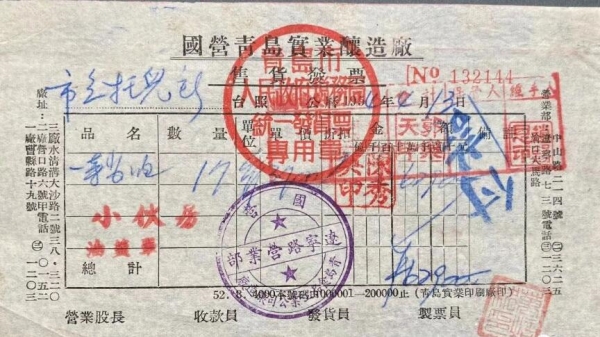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