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成书的《胶澳志》,记载平原路的长度444.32公尺。德占时期叫理萨街,日占时期叫鞍马町。但以时下的步子丈量,原先的路长最多到今天39-64号的位置。
平原路的起始路牌,立在与沂水路相接的路口。江苏路与平原路、加上山大医院门口的一小段路围起来的三角地,曾经是街道办的一家饭店。在饭店门口东望,江苏路与龙口路的两条岔路形成的是另一处三角地。在江苏路的街边,那曾经还是1路环形车的公交站点。
山大医院入口大门的左侧,承担传达室功能的德式建筑物,有着红瓦的屋顶和墨绿的门窗。大门再往西以及沿着平原路小上坡北行走到医院的后门,都是菱形铁网形成的半圈围墙。当顺着平原路上下行走时,透过铁网,院内的建筑物便可一览无余。
这种铁网到底是经过冲压还是焊接而成,那时是未曾去想象的问题。五六米一段的铁网,由一根根柱子前后相互连接。高出铁网的柱子,由石材和红砖堆砌而成。柱头的收尾以瓦片装饰、形成屋檐状,看起来更具欧洲风韵。
刚上了小学的时候,大约是透着春寒的一个周日。妈妈因为上班而缺席的全家外出,在我们从海边儿顺着江苏路走上来的时候,正好就在山大医院大门的左侧石头沿儿上休息了片刻。
奶奶和妹妹先坐下,爸爸说给我们拍张照片,让我也坐过去。在按下快门之前,爸爸说我靠得奶奶太近了。虽然外移了一点,但照片洗出来后,还是发觉是倚靠着奶奶的样子。妹妹的状态很独立,虽然时不时她还要大人抱。如果没在这里拍照的话,对于铁网的围墙还真的没了记忆的参照。
如今的医院,成了人满为患的地方。人多,自然车也无处停放。每每早上的时间,江苏路周边的交通堵塞极其严重。求医问药找医生,路面维序靠警察。两种职业两个群体,肩负着同样的与治病救人相关和相当的社会责任。
当年拍照时的围墙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地铁的B1出入口。有B1就有B2,或许将来还会有B3。同样的B,若是选择一二时出现模糊,出地面的偏差就要三四五六。如此设置,必有原委;习以为常,不容质疑。
平原路一侧的围墙式样,目前已换作像是铸铁件的图案化设计。行至半程的位置,是一处“不对外开放”的内部停车场。医院停车场前行30米的右拐箭头,值得深刻地领悟。否则,还是进了不对外开放、只对内搞活的专用场所。
实际上,停车场的所在地点,是六十年代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开挖的防空洞后,建成的地下战备医院。这处近17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在1968年由市人防指挥部移交给医院,并且还进行过短暂的运营。1979年,又交还给人防部门。至八十年代初,这里专程破墙作为进出的通道,做过旅馆住宿的经营项目。

再上行四五十米,是医院的后门。幼年与小伙伴们在医院的内外穿梭玩耍,始终没有掌握后门什么时候开放的时间规律。开着门就进,否则只能走正门。那时医院还是相对空荡的,有几排弧形屋顶、灰色油漆涂刷的临时建筑物。稍大年龄的孩子解释,德国鬼子当年没打算在青岛长呆,所以在医院设立了不少这种简易的房屋。
医院的后门往北,是一竖排二层的楼房,应当是平原路单号的起点。前面的几个门牌中,有修瑞娟的故居。二中毕业的修瑞娟,八十年代初成为世界微循环领域的专家。这排居民楼的北端,是相连着的砖红医院围墙。与南半段的铁网不同,这里的砖墙看不到院内的任何风景。只有走到坡上时,矗立在路边、带着两扇大门的太平间,让人不由地肃然起敬。
太平间以南的这段红墙,大约三四十米的距离。墙的中间部位,有个医院内垃圾的外卸出口。有段时间,经常能够路遇一位手推左右筐推车、从坡下匆匆走上来的收垃圾的中年人。巧的是,有次爸爸领着我在玉生池洗澡,在快下班的时候,我们的隔壁床来的正好是这位拾垃圾者。大人的谈话,小孩并未在意。只是知晓,他要晚上在澡堂子里住一宿过夜。
时至今日,他的面孔依旧记在心底。前额稍显微秃,两腮总有胡须。当年不管是拾垃圾还是扫大街、刷厕所还是掏大粪,那个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年代,或许都有一种特殊的背景和特殊的身份。一事不解,万物皆谜。
著名画家王海宁先生的《老墙记录》,创作于1983年。这幅55 x 39.5厘米的水粉画,堪称给山大医院留下的珍贵资料。在没有历史影像的情况下,美术作品成了最好的档案资料。
现在的墙体,都是通透的金属围墙。沿街的楼房拆了,腾出来的空地给了拥挤的一栋栋病房大楼。太平间也是原地重建,完全失去老建筑本身的价值。作为彼时幼童,难解生死离别。而今少有途经,却偶然走过。看着烟熏火燎的怀念堂三个字,想到的只有回忆录一件事。
老墙画作,已成绝唱。注目半条马路,只剩回味无数。
原载 rossen
2024年09月21日 00:00 山东
张勇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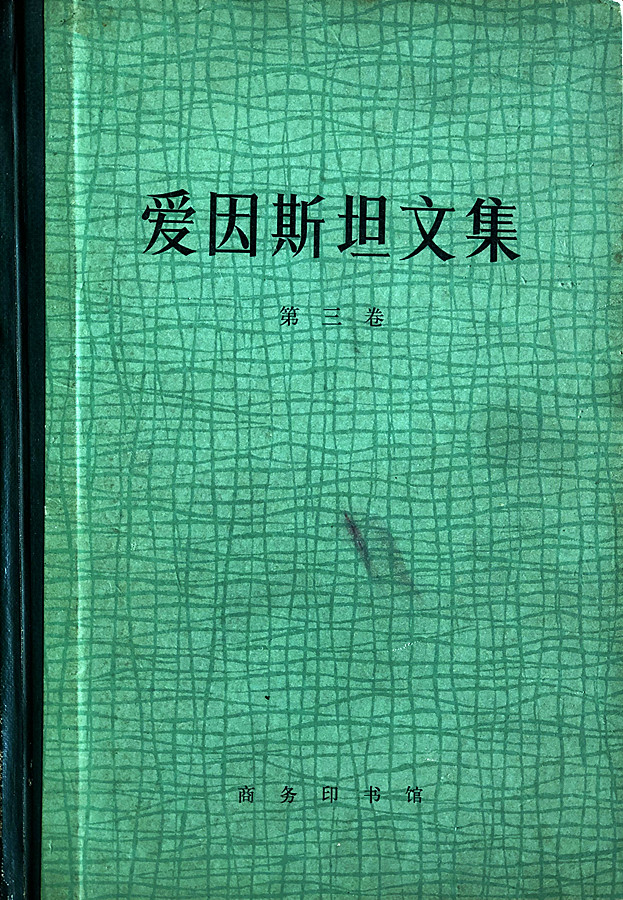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