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填写志愿时,我和同班Q同学完全相同,第一表第一志愿是北京医学院,第二志愿是山东海洋学院生物系;第二表仅填山东医学院医疗系。结果我被第二表录取,后来做了医生,而“小拳头”被第一表的山东海洋学院录取,后来当了老师、校长。
1963年夏,我离开青岛,在济南开始了长达7年的大学生活。青岛二中考入山东医学院的学生共两男一女。开学分班,我和男同学在63级三班,1965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要“掺砂子”,“砂子”就是城市学生,班级调整时,我们二人又一起到了63年级四班。高中、大学都一个班,调班还调在一起,实属有缘。而我和另一女同学的缘分更深,结成一生一世的姻缘。
得知自己考上大学,是父亲电报通知我的,因我那时正在掖县老家。电报到时我正和爷爷在房顶上修理漏屋,我几乎是从高梯子上飞奔而下,当时如果摔断了腿也不奇怪,学生对上大学的渴望,金榜题名时的激动,只有过来人才有体会,要不范进中举后怎么能疯了呢?离大学报到时间已经很近。我拿着爷爷解放前从哈尔滨带回的旧柳条箱,还有一个他自制的盛照相器材的带锁小木箱,立即返回青岛。我的衣服被褥很简单,日记本和集邮册,以及不多的图书是我的全部家当,开学前兴冲冲坐火车奔赴济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家外出。
8月底来到泉城济南,这座城市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读过清末小说《老残游记》,书中对济南做了详尽的描述。为了身临其境体验书中情景,我与二中校友同游趵突泉和千佛山。山东医学院南墙外就是千佛山山麓,我们兴致勃勃拾梯而上,山岩上雕刻着大大小小很多立体佛像。在半山腰的山门外见一茶摊,摆着十几个玻璃罐头瓶盛着的凉茶,我问光头摊主:
“请问,千佛山有和尚吗?”
“当然有!”
“和尚在哪儿?”
“那是你不找。”
“庙里没有,到哪儿去找?”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就是!”
“你?你不是在卖茶吗?”
“社会主义的和尚也要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听罢我顿时醒悟。
千佛山山石上凿刻有成百上千的石佛,和我一样在默默聆听这思想改造的伟大成果。谁会想到3年后的1966年,因为思想改造还不彻底,“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将石佛像统统砸毁,这下完全彻底了!估计那位已改造得不错的和尚也逃不掉,他是死是活无从考究。现在即便寺庙重修,和尚重返,但千年的千尊佛也像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一样永远消失了。人们都说物是人非,现在倒成了人是物非。在中国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年代中,斗来斗去,天、地、人皆伤痕累累,累累伤痕,人和物甚至万劫不复,可恨可叹!
山东医学院的前身是齐鲁大学医科,齐鲁大学是1904年由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14个基督教会组织联合开办的。全称是“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当年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1952年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省立医学院和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合并成立山东医学院,11年后我也金榜题名考进来了。刚进大学时每月饭费11元,我的家庭条件自然不能享受助学金,父亲每月给我邮寄16元人民币,20岁时终于有了5元零花钱。记得第一个月花费超标准,原因是自作主张买了一双元宝式样水胶鞋,那时还没有塑料凉鞋,长这么大头一次下雨穿水鞋,脚是舒服了,可张口多要钱当然引得父母不满。大概是入学第二年,饭费提到14元,于是父亲每月给我寄19元的生活费,取钱时被同学看到,他们不解为何不寄20元整数,教授老爸多一元也不给?是的,多一元也不给!但不给我也没意见,父亲一人要养活老少三辈一大家人,实实在在很累,很辛苦。而我成年了还在消费,自感有愧于父母,但那个年代除了助学金外,既没有奖学金,也没有勤工俭学,学生只能靠家庭。特别是“文革”让我们在学校待了整整7年,不但不挣钱,反而倒贴钱,无所作为地混日子,花家中的银子在校“斗、批、改”,这让我对父亲对家庭有一种负罪感,当然对发动“文革”误人子弟的人,对那位曾在心中奉若神明的人也渐渐产生了仇视感。这真应了他那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现在回想这段历史,真应该一起去申请国家赔偿,我们山医63级的学生,损失太大太大了,7年大学生活,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损失,都很难算出确切的数字。
我们那时在校吃饭十人一桌,一盆大锅菜平均分配,馒头或窝窝头一人一个,星期天休息可以退伙,但同学退伙的目的并非为了外出改善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省出这几元钱来买笔墨纸张,因为当时同学家中都不富裕,即便享有全额助学金者仍感生活困难,不得不出此下策。同学中有偷衣服偷鞋的,有偷书偷笔偷本子的,甚至有偷国旗做褥子的事,现在讲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可当年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人穷志短,为了吃饱饭,女大学生竟然嫁给伙房炊事员,这并非天方夜谭,山医食堂的厨师就当着我们的面宣扬过自己的婚姻交易。
当年大学生活十分枯燥无味,每天宿舍、食堂、教室三点循环,周末能在大礼堂看场电影就算莫大精神享受了。清晨做操,食堂吃饭,教室上课,9点
下晚自习,9点半宿舍准时熄灯,行动都是半军事化。基础课的高等数学和物理化学我都没好好学,有的考及格,有的考良好,考优的很少,我认为对学医来说无关紧要。对组织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就相对重视一些,自己计划要把精力放到临床课,不料临床课不久就遇上“文革”,被迫去学工学农学军,医学院学生硬是不让学医,岂不咄咄怪事?
大学一入学就宣布纪律,学生不准谈恋爱。星期天干什么?济南市的大街小巷我都已走遍,大明湖、趵突泉等名胜都已游完,图书馆除业务书外没有几本有趣的可读之书,文化生活单调可怜,许多同学蒙头睡大觉。而我却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八一礼堂南的省军区大院。舅舅家的大表兄从小跟姥娘和我母亲生活,与我们感情很深,好像我们才是一家人。1949年他参军入伍随部队南下,在福建剿过匪,吃过猴脑,后调北京军区水陆坦克部队,开车在內蒙古草原打过黄羊……我上大学时,他恰恰又调到济南。表兄当时单身,对我的款待诚心诚意,周日约我去部队,鸡鸭鱼肉非让我吃了再吃,生怕我客气不好意思,每次都让我吃到脖梗要吐出为止。我在他宿舍里喝啤酒是生平第一次,感觉真像马尿味道,来自啤酒之乡的大青年,在青岛却从未品尝过啤酒,现在的青年肯定认为我在说谎,可在我们这个家庭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万事不求人的父亲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我自然也就接触不到烟酒了。我真正吸香烟喝白酒是分配到公社医院之后,是经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那时才知道什么是“吃香的喝辣的”。
在学校第一次下乡是到城南,一个缺水的山村,农民将雨水和雪水收集在井中或坑中,沉淀后饮用。干旱带来的自然是贫穷,尽管头顶“三面红旗”也照样不管用。我们学校每天用消防车拉水,一人一杯刷牙水,几人半盆洗脸水,这种待遇引得社员羡慕不已,看着清澈的水被吐掉倒掉,村民十分心痛。我们帮社员春耕春播,目的是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此来提高大学生的阶级觉悟,可一周的“三同”并未大功告成,回校的全院总结大会上,基础部书记孙绪峰讲:“有的同学阶级立场不清,替富农分子挑水。”这是指我班那学雷锋做好事的同学。“有的同学称呼不看清对象,本是姑娘硬叫人家大嫂。”这就是我的囧事。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我要求自己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凡事应当三思而后行,避免祸从口出。
我入大学时已20周岁了,可并未谈过一次恋爱,哪像现在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不管在马路上还是公交车内,又拥又抱,又亲又咬,自由得没法再自由。山医大院女生最多,不像山工、山大、山财,女孩子寥寥无几,虽说“不准谈恋爱”的纪律像利剑悬在头顶,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时处处面对约占三分之一多的女生,春心难免不动。不知为什么,让我心动的女孩子大都是高年级的,也可能是城市女生都集中到61~62年级的原因吧。这种一厢情愿不应称作恋爱,严格讲只不过是对女性美的一种追求罢了。我这人处世认真,爱动笔墨,感情的事都用诗词做了记载。
刚入学时,副院长方春望在大会上讲,全国12所6年制医学院,将来和8年制的医科大学一样待遇,毕业后有“三大三小”等着我们。然而这句话后来却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言辞,“文革”期间翻来覆去批判的主要内容,方院长也成为“文革”中第二个揪出来批斗的院领导,遭罪受辱程度仅次于王哲院长。然而,毕业后补发的毕业证书上还是盖着方春望的大印,他不单没有被打倒,反而由副转正了,这恐怕谁都没想到,你说滑稽不滑稽?可笑不可笑?当年的王哲院长平时很少见到,他是9级干部,据说和省长平级,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是蒋经国的班长,真是老革命了,可“文革”中却成了山医的头号走资派,1966年9月5日就被早早揪出来,七斗八斗,于是也早早一命呜呼!
大专院校是“文革”发源地,红卫兵是急先锋,我1966年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红海洋见过周总理,在24天大串联中从北国到江南。当时我狂热地参与过,过后冷静地思索过,既爱过,也恨过。这历史一页我将单独记录。
1970年夏,我们终于毕业分配了。6年制拖到7年,不给毕业证书,更没有学位,一鞭子赶到公社医院。按正常的学制,研究生也该早毕业了,可我们偏偏成了最倒霉的一届,甚至影响到以后提工资、晋职称。
呜呼!大学,我的大学,我们不堪回首的全国首届七年制大学。
原载轻博客
12/30/201912/30/2019 10:35:18 PM
史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特别声明:本文丛作品多为原创,版权所有;特殊情况会在文末标注,如有侵权,请与编辑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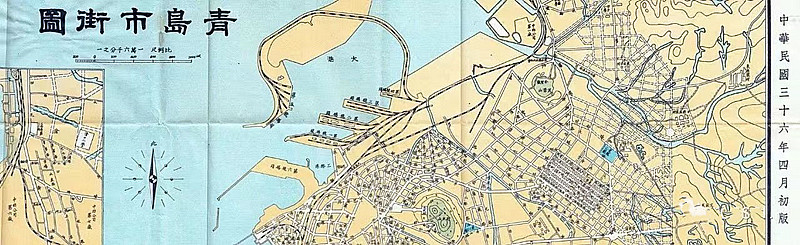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