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乐是得胜的记号。2019年5月的最后一天,给我们喜乐的平凡生活平添了沁人心脾的馨香:我们拥有了两盆栀子花。这两盆栀子花也许等了我们很久,在花农的大棚里,在熙熙攘攘的集市……它们也许听到太多的品头论足,说它单调的白,无法装饰迎客大道上的姹紫嫣红;嫌她只有两片花瓣,显得单薄;嫌她花期短,不似月季……她们静静地守在那个废橡胶做的花盆里,丝毫不为这些品评所摇动,花容淡然,默默地吐着芬芳。花的世界哪有人类社会的风云多变心随世转?花木各从其类,遵守生命律例,开放凋谢,去留无意,用纯真的美丽无怨无悔地美化着这个被人类轻贱损坏的自然世界。
这两盆栀子花是在距市里三十多公里的惜福镇集市上买的。惜福镇,多么美好的名字!表达了乡亲们祖祖辈辈实实在在的生活愿望。这里的集市承继了过往的规定:每逢农历的二、七是惜福镇的集。市区不乏大大小小的超市,各种日用品应有尽有。而这每隔五天就有的农村集市,仍然人来人往,热热闹闹,赶集给了我一种回乡的感觉……
我尾随着丈夫,在拥挤的人群里穿过卖布的、卖盖垫的、卖农具的,直奔卖花的摊点。该是栀子花先看见了我们吧,一阵阵浓郁的花香是在发出呼唤吗?就这样,在无数盆栀子花中,这两盆栀子花告别了她们的姐妹,像优雅的少女被小心翼翼地接进了我们的车子里。
回家的路,满载着我内心的喜悦。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有我信赖一生的人把握方向盘,我可以无忧无虑,微闭双眼,品味客旅行进的超逸。
栀子花的香气是从我背后飘来的。我回头一看,哦,我年轻的妈妈正从村口跑出来,“小闺女,小闺女,我有要紧的事告诉你!”那个四岁的小女孩是我吗?她欢快地向妈妈跑去,跑到跟前,正想扑到妈妈的怀里,才看见妈妈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她心疼妈妈,扯着妈妈的衣襟,央求着:“妈妈,快放下包袱,小闺女和你一起抬。”妈妈费力地把包袱放下,弯着腰亲着小女孩的脸,轻声说:“好孩子,你抬不动。妈妈要到区里送军鞋。你爸爸在前方打鬼子,等着穿呢!”小女孩摇着妈妈的手:“我也去,我能抬动。”
妈妈抚摸着她的头发,细声说:“妈能背动。你听话,在家看门。你大姑和我一起去,你得在家帮着你舍姐看小业弟。”她直起腰来,仰脸看着远处,一会儿又弯下腰亲着小女孩,说:“等你爸爸打跑了日本鬼子,和你姑父扛着枪回来,我就告诉他们,小闺女是好孩子,是听话的好孩子,舍子也是好孩子……”
妈妈还说了好多话,依稀记得这么几句,别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一天妈妈和大姑都穿着新衣裳,看上去是那么漂亮。妈妈上身穿着鸭蛋青色的短袖右襟小褂,下身是仁丹士林的长裤,裤腿肥肥大大。大姑上身穿月白色的右襟短袖小褂,下身也是裤腿肥肥大大的仁丹士林裤子。最好看的是她们的头发:齐肩的黑发,有一缕头发从白净的额头卷到头顶,用卡子卡得紧紧的。就像茶叶盒上画的漂亮女人的头型,我们小孩管这叫飞机头。她俩每人的发卡上都卡着一朵鲜花。大姑卡的是一朵艳红的石榴花,妈妈卡的是洁白的栀子花。
舍姐牵着我的手,站在乡间的小路上看她们远去。天空又高又蓝,间或有几朵白云展翅而过,午后的阳光在静谧的乡间照耀,远处的树像披着闪闪的金纱,零星地耸立在草丛和田埂间。小路两边的青草随风起伏,淹没了弯曲细长的小路。我妈妈和大姑每人挎着一个大包袱,妈妈走在前面,大姑跟在后面,远看不像是在走路,倒像是绿浪推着她们向前奔去。肥大的仁丹士林裤子被风吹起,像碧蓝的波峰;妈妈和大姑的小褂,像鼓满风的白帆;飞扬的黑发上明丽的小花,渐渐地变成了两个亮点,闪耀在广袤的天地间……
面对这往昔清晰而生动的场景,今天的我为什么泪流满面?是的,我泪如泉涌。75年前的那个小女孩,并没有哭。在那个栀子花开的春天,她不会想到历史和岁月会发生怎样的惊世突变,不会想到妈妈和大姑会遭遇什么。她单纯的心里唯一藏着的是妈妈的梦想:多做军鞋,多送军衣,爸爸就能快点赶走日本鬼子,早点回家。那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时刻,无论是母亲,还是孩子,心里都满怀着定准于未来的欢喜。因为彼时,故事的结局还没有到来。
我和舍姐抻长脖子,看着妈妈和大姑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影儿了,舍姐才贴着我的耳朵说:“俺妈偷着告诉我,她们今天能看见和爸爸一块打仗的叔叔,是从前线回来拿军衣的。俺妈说,我和你舅妈都打扮得俊点,叫人家回去告诉你爸他们,说俺们在家过得挺好,你们在外面好好打仗,不用挂牵家里。这不,她们穿得多好看!”舍姐说完了,还扭头向四周看了看,又叮嘱我:“你管谁也别说呀,俺妈说了,叫人家知道了不好!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点了点头,舍姐拉起我的手,学着大人的样子,勾了勾我的小手指。舍姐大我四岁,是我大姑的长女。那年她八岁。
七十多年来,这个场景从来没有在我心里出现过。记忆的苏醒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有时,可能是一线阳光,一片落叶;抑或一种声音,一缕气味,洞穿记忆的隧道,沉睡的往事蓦然醒来。
感谢这两盆栀子花,飘来七十年前栀子花清雅的花香,让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了我年轻的妈妈。
她是那样美丽:高挑婀娜的身材,白净如栀子花的皮肤,微微上挑的眉毛下一双含笑的明眸。她的牙齿齐整洁白,像饱满的石榴籽一样晶莹。妈妈的一口牙,为了做军鞋没少出力。铺鞋底的布要自己织。冬天的夜弯弯的月牙看着静谧的小村庄,我睡得迷迷糊糊,用手一摸,妈妈不在身边,我知道妈妈又在边屋织布了。妈妈织布时,不光用脚踩机,用手抛梭,还得用牙。有时,经线断了,妈妈用针挑起断头,用牙咬紧,抽出另一边的断头,把两根断头在嘴里轻咬以后,才用针挑着接起来,再趴在织机上,用门牙把接头咬平,才能放进去。梭子拖着纬线,在经线里抛来抛去,妈妈说,断线是常事,她还得用牙把断线咬润,用针剔去粗绒,才能把线头接好。接好后再用前牙咬平,放回梭子,织出的布才看不出接头。
布织好后,用浆糊粘成布壳铺成鞋底,纳鞋底的苘麻麻绳也是自己搓出来的。秋天苘麻成熟了,妈妈和大姑把砍断的苘麻杆拉回家,泡在大盆里,两三天后捞出来用棒槌轻敲,洗衣的棒槌是木头的,敲到皮枝分离,然后用小刀切口,轻轻剥下苘麻皮,等它快干时,再用棒槌反复轻敲,把外皮敲细,用水淘净,剩下的就是苘麻纤维。在我们那个小山村里,只有我妈妈会用苘麻搓绳。妈妈说,这还是她当了妇救会长以后,因为做军鞋需要才从我姑姥姥(妈妈的亲姑)学来的。苘麻粗糙,不能用纺花机纺,也不能用线砣转,只能用手搓。姑姥姥夸妈妈手巧,搓得又快又匀和。妈妈笑着告诉我姑姥姥:哪里是我的手巧,是我的牙好哇!苘麻光用水泡搓不好。我搓的每一根麻绳都用水泡过以后,一缕缕用牙咬了才搓的!
此刻,我清晰地看到了妈妈的手,那双搓苘麻绳的手,日复一日地搓,已经搓得没有了指纹。
馨香的栀子花啊,是什么让我忘记了年轻时的妈妈?
车子突然慢了下来,我抬头一看,收费站到了。"城阳南"三个红色大字高傲地支在收费站的顶棚上,好像在提醒司机:你要上高速了!ETC电子收费,栏杆自动升起,车子不须停车,径直通过,迅速提速,一会儿时间,就达到时速120公里。高速公路,速度就是快啊。
妈妈当年送军鞋,要是有现在的交通该多好!她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汽车,她们只能靠两条腿奔波在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
妈妈舍不得占用下地干活的时间,到区里送军鞋多是下午去。等验完军鞋赶回家已是月上中天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大姑家的炕上,不知道妈妈几时来接的我。依稀记得朦胧中,妈妈抱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我的脸紧紧贴着妈妈的脖子,栀子花的清香萦绕着我,我感到很舒适,很舒适……
汽车飞奔在高速路上。中午的阳光有些灼热,坐在车里,有一种似火烧的感觉。丈夫先是打开车窗,发现风太大,怕吹着我,又旋即关上;抬手打开天窗,顿时,一股清凉的风吹进来。栀子花香骤然在车厢里弥漫,香气从四面八方扑来,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我推进童年的天地……
小时,我常听大人们说:年轻人都走了,村子凉了。我不懂凉了是什么意思,妈妈告诉我就是人少不热闹了。她说她十九岁嫁到我们家时,村里很热闹。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闻名的中医,他看病的厅堂有七八间房子那么大,平时总是人来人往。到了晚上更热闹,本村外村的年轻人都聚到爷爷的厅堂里,跟爷爷学拉胡琴、吹笛子、吹唢呐……过年还在打麦场上扎戏台,演大戏。
战争破坏了我们这个小山村平静安稳的生活。
妈妈结婚不到一年,我爸爸和这群在一起吹拉弹唱的年轻人,还有村里几乎全部青年男女,撇家舍业,奔赴抗日最前线。仅我们家族,就有26个亲人离家从戎。村里除了老弱病残,剩下只有四个带孩子的年轻妈妈:我妈妈最年轻,20岁,我刚出生还没满月;我爷爷小堂弟的妻子,我叫她禛婆,23岁,有三个孩子;我大姑,23岁,有四个孩子,姑父参军后,她就长期住在娘家;村东头的桂姨,21岁,丈夫当兵后,她带着一个女儿,回到娘家来住。遥远的战火点燃了她们内心的青春激情,四个人都参加了“中国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我年轻的妈妈被指定为妇救会会长。她和三个会友担负起小山村十几户军属的农耕农作和缝军衣、做军鞋支援前线的重担。
我三岁以前是怎样过的,没有印象。我三岁以后最深的记忆是:爸爸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前线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妈妈们在后方,后方也是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她们每天一早就走了,到后方去了,日头偏西才回来。
我和村里这八九个孩子一整天满村串着玩。
玩什么呢?没有玩具,也不知道什么是玩具。我们玩打鬼子的游戏,找两根木棍当枪,拿枪的是八路,不拿枪的是鬼子。我们没见过枪,不知道枪隔着很远就能打死人。我们是拖着棍子跑,撵上“鬼子”碰他一下,他就得死了。我经常当“鬼子”,因为我最小,跑不快。我拿枪时,好几次明明看见“鬼子”藏在第二街,可就是撵不上,白白让“鬼子”跑了。这个游戏总也玩不腻。因为拿枪的和鬼子要换着来。七八个孩子,一共两支枪。枪少“鬼子”多,要把“鬼子”全打死,有时打半天,都跑累了,靠近谁家,就到谁家吃饭,饭几乎都是一样的:玉米面饼子、地瓜干。妈妈们早晨蒸好,锅底烧上水,温热着箅子上面的饼子和地瓜干,一碗拌好的萝卜咸菜,放在锅台上。
玩一上午,手应该很脏了吧,也没有洗手一说,拉开锅盖,一窝蜂地挤到锅台前,用手抓着饼子地瓜干捏着咸菜吃得很香,渴了,用瓢在水缸里舀一瓢水大家一起喝。要是锅里空了,有谁还没吃饱,我们拉起枪换一家,还是一样的饭。直到每个人的肚子饱饱的,才罢休。
20世纪的1965年,我国进入全民皆兵的年代,我即将走出大学校门之前,扛起了真枪学习打靶。二十年后,在我们练枪法的靶场盖起了一座大学,我曾在那里任教。坐学校的班车回家,我常常看着学生们衣着鲜艳地踱步在花间树下,有的交谈,有的背诵着什么。我心里总是想:和平对于人类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往昔在这里打靶的场面在我眼前一闪,孩提时拖着棍子打日本鬼子的嬉闹声也尾随而至。在那一次又一次的游戏里,日本鬼子,在我们心里模糊而又陌生。我们只有一个美好心愿:快快把鬼子撵走,父亲就能回家,全家一起高高兴兴过日子。彼时,战争,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遥远抽象的词。我们不知道战争会死人,然而,母亲们知道。过不了几年,当战争延续至另一个场景,我们这些孩子才真正感受到了战争的另一种严酷。
我无忧无虑欢快无知的童年啊……
记不清有多少个夏日的夜晚,裹着满院的栀子花香,我们几个孩子趴在大姑住房的窗外,听妈妈们的悄悄话。那时住房的窗户是木格上贴着窗纸,看不见里面的人,可谁说的什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窗台不高,大点的孩子把胳膊支在窗台上,我和富莉姑个子小,得跷着脚才能够着窗台,舍姐早就把家里的小板凳拿出两个,我和富莉姑站在小板凳上,两个胳膊就能趴在窗台上了。夜里的蚊子很多,蚊子咬了就用手蘸点唾沫摁在蚊子咬的地方,用指甲掐掐,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生怕出声叫妈妈们听见就不说了。
偷听来的这些悄悄话,在我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以至到六十岁从来没有想过,好像我不曾听到过一样。生命真是奇迹,它储存着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是在人不经意的时候悄然出现。旺盛的生命在日常生活里进展奔波时,记忆却在时光的长河里沉睡。可当我进入暮年,许多孩提时的记忆,像清纯美丽的浪花,间或从时光的长河里迸跳出来。此刻妈妈们的悄悄话就像水珠四溅的浪花扑到我面前。我说它水珠四溅,不是指往昔的波浪奔流前进,被今天黑漆漆的大门撞碎而溅出四散的水珠。心灵的记忆是锚定在万古磐石之上的,它可以在时光的长河里随性迸跳,展示它本真的美好!没有什么能撞碎它。扑到我面前四溅的水珠,是我孩提时的零散记忆,而那些美丽的浪花则是妈妈的补充述说积淀在我心底永不变色的往事,它总是那样栩栩如生带着故土的乡音悄然而至。四五岁的孩子心里留下的都是当时觉得好玩的,奇怪的。像我爸爸说我妈“你是我的栀子花”,姑父叫大姑是“我心上的石榴花”!禛爷和我禛婆是凤凰变得吗?人家都盼丈夫早点回家过好日子,我桂姨怎么盼丈夫回来打她?
这些不明白的事,要是妈妈事后不告诉我,我至今都不会想到其中隐含着年轻妈妈们对丈夫多少思念,对婚姻是多么的忠贞专一,对家庭和美生活发自肺腑的无限渴盼!
妈妈告诉我:怎么说起栀子花的?是那天晚上缝军衣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在回忆结婚那天晚上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我就说,是闹房的人都走了,你爸抱我进屋的时候,对着迎门的大镜子,他说:看你,就像咱家栀子花一样,又香又白!
我记得我听到这,还说:妈,我爸真有劲,能抱动你。等他回来,我叫爸爸抱抱我!
姑父怎么把大姑当成心里的石榴花?我妈妈说,他俩的婚事咱村的人都知道,是石榴牵的红线。你大姑人长得漂亮,手又巧,每天大门不出坐在家里绣花绣鸟,累了就到院子里的石榴下站会儿。那时咱家是南北两个院子,南院是住房,北院是药房。过道连着两个院子,外人要去找你爷看病,不能从住家的过道走,得穿过东街转到北街,进到药房。有一天,你大姑站在南院的石榴树下,手拉着一根树枝端详上面的花,突然一个小伙子闯进院子,嘴里还喊道:大伯,大伯,俺爹叫我晚上跟你学琴!大姑惊得没松手就扭身要往屋里跑,不想树枝恰巧勒在她脖子上,没等她迈步,小伙子一个箭步冲过来,拦腰抱住了她,这才救了她没跌倒,没勒伤。大姑羞得不敢抬头,小伙子也痴痴地看着她,好半天没说出话。第二天媒人就来了,两家老人都熟,不到一个月就成亲了。你大姑说,你姑父就叫她石榴花。参军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还拉着她的手到石榴树下,嘱咐她:“等我呀,等打走鬼子我赶快回来,咱俩坐在石榴树下,我拉胡琴给你听。养护孩子,过好日子。”我记得妈妈告诉我这些事时,声调又轻柔又深情,好像说的不是大姑,是说她自己一样。是啊,我妈和我的大姑、禛婆、桂姨已经超越了亲戚邻居的情感,十几户军属的农活她们全部包揽下来,四个人天一露亮就起来,扛着镢头、锨,带着干粮上坡里,一干大半天,日头偏西赶回家,给孩子们做饭,晚上又聚到大姑屋里,点着两盏小油灯缝军衣,做军鞋。她们相互依靠,彼此信任,不管担子多重,生活多艰难,表露在外面的,都是笑容满面。内心的压抑,既不能向外人说,更不能让孩子知道。她们不愿意让孩子小小的年龄就背上大人的困惑。唯一支撑她们的是简单朴素的感情,丈夫提着脑袋在前方打仗,她们再苦再累也要拼尽全力地干。她们简单朴素的情感和远方的丈夫紧紧连在一起。没有人纪念这些不见经传的年轻妈妈,为爱情、为家庭、为孩子默默做出怎样的奉献!她们心里想的是爱,身体力行的是爱,平日教导孩子的是爱,甚至她们在一起说的悄悄话也是爱!她们是一代无私奉献的母亲,比起当今那些影视上难舍难离缠绵歌曲一波三折掏心倾诉的爱情,她们朴素坚贞不曾言说的大爱更接近心灵的本真。
妈妈对我讲禛婆和桂姨的时候是在一个凄风苦雨的晚上,是在大姑落难,祯婆西去、桂姨失踪以后,妈妈带着我躲在山里的一间废弃的土坯屋里。贫穷的山村,消息十分闭塞。这四个活跃在和睦村邻中的年轻妈妈,她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人世间会有那样的败类,国难当头,他们不去前方打仗,却到后方强抢豪夺,用谎言欺诈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那是麦收季节,她们四个人没白没黑地抢好天气把麦子收回来,像男人一样在打麦场上,打麦、扬场,把各家的麦子送到各家的粮仓里。地里的活抢收完了,她们在禛婆家休息。禛爷是读书人,参军前是完小的老师,家里书多。禛婆有不少绣花的花样,夹在几本厚皮书里。她们正翻着书找花样的功夫,闯进几个大男人,叫着我大姑的名字,说婆家村里的人听说大姑在这里干得好,叫她回去介绍经验,说说是怎么拥军优属的,大姑推辞了半天,对方说,村里的人都在学校等着,催她快走叫她把孩子带上。我们村到大姑的婆家,有四十里路,大姑就跟着他们走了。我妈她们没当回事,可第二天一早那几个人又闯到禛婆家,说要借花样看看。祯婆忙不迭地把几本花样书都搬出来。祯婆不识字,她只知道这是禛爷在外地上大学用的书,觉得没有用了,书皮又厚,就用它夹花样。那几个人挑了其中的一本连花样带走了,说用完就还回来。谁知几天后从外面来了十几个男子汉,挨家挨户把村民叫到村南的打麦场,说有要紧的事告诉大家。村里能去的人不多,我们家是我爷爷去的。那天正是我和妈妈在姥姥家住了几天,吃过午饭往回赶,到家已经黑天了。爷爷把我妈妈叫到他房里,悄声告诉白天发生的事:那些人把禛爷的书给大家看,说禛爷是特务。这本外国书就是证据,逼着禛婆交代。禛婆说这是他上学时的书,他们打了祯婆,还撕裂她的上衣,当着大伙的面把手伸到衣服里,小富莉吓得扑到她妈的怀里,那个人还打了富莉。村里的老少爷们看不下去,村东桂他爹吆喝一声:“青天白日的这是弄么!人家是妇救会的!”又有几个人说:“她是妇救会的,俺这个村的,她谁没帮扶过!”他们当中有个捆腰带的人摆摆手说:“散会散会,明天再说。”当天晚上,妈妈叫我好好睡觉,她急匆匆地去看祯婆了。第二天,那帮强盗踢开祯婆家的大门,冲进正房又倒退出来—祯婆和她的小女儿富莉双双吊死在屋梁上。祯婆穿着结婚时的红绸子嫁衣,脚穿凤凰绣花鞋,上衣、裤子、袜子和鞋都用针线密密地缝在一起。富莉姑穿着粉红小褂绿花裙,脚穿绣花小鞋,锅台上有半碗温热的鸡蛋汤……
人没了,他们翻箱倒柜,凡能拿的衣物、器具,全部掠走了!
妈妈每讲禛婆的过世,都泣不成声。她说,那天晚上她去禛婆家,禛婆告诉她:我不能活下去任人糟蹋。我只属于你禛叔。他告诉我,他是凤我是凰,我俩一块就是凤凰,只有死能把我们分开。要是有一天你能见到你叔,告诉他我守住了节操,死也是他的人!富莉太小,留着那些人也不知怎么糟践她,我把她带走!还有两个孩子,我叫他们上他姥姥家,往后你多帮扶帮扶他们……其实,禛婆出事的那夜,妈妈和我都没睡好。天刚亮,妈就带我到姑姥姥家。姑姥姥的家在这一排房子最西头,院墙的西边是村里唯一的一条南北路。东院墙是禛婆家的西院墙,两家紧挨着。妈妈和姑姥姥还到祯禛家推了推院门,见没有动静,便悄声回来了。
我心里憋闷,我不知会出什么事,便躲在姑姥姥家西山墙外,时不时探着头望禛婆家的门。村里人少,山墙外的这条路平时来往的人不多,我和富莉姑常在这里画格格跳房。富莉姑说话细声细气,跳房的沙布袋,有时扔到方格外,她就叫她家的小巴狗去叼回来。小巴狗很乖巧,叼过沙布袋吐到富莉的脚下,总要用爪子搔搔富莉姑的脚背,富莉姑就弯下身抱起它,摸摸它的耳朵再放下。它就老老实实蹲在墙根看我们跳房。我躲在山墙旁,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突然看见有五个男人,从南边一路小跑直奔禛婆家,我听见他们骂骂咧咧地踢开祯婆家的大门。突然,小巴狗窜出来,它一眼看见我,就咬着我的裤腿拖我,向祯婆家走,它看我向前走了,就松开嘴,一溜风钻进祯婆家,随着吼骂,我听见小巴狗凄惨地大叫了一声,再也不见它的踪影……后来听人说,这些人是畜生,没有人性,连只小狗都不放过,竟把小狗的脑浆和眼球都蹂黏了……
栀子花啊,亲爱的栀子花,你们怎么啦,娇嫩的花瓣为什么颤抖?花木有自己的情感,也有自己的历史,花木的历史必定和人类的历史不同,人类的历史未必记载历史真相;而花木的历史是无数花木茎叶相传落入泥土积淀而成。风是花木的信使,此刻,风随着自己的意思携来花木的历史,摇撼着栀子花的情感,是哪些历史呢?是由人类荒蛮贪婪造成的花木伤害史吗?你是不是为我大姑的石榴花而悲伤?
是的,花木的历史会真实地记载:我大姑是被骗回去的。姑父的高祖曾做过咸丰皇帝的老师。那些强盗为了掠夺财物,把姑父家所有的人都打死了。容我大姑存活,是他们中有一个比我大姑大30多岁的鳏夫,见我大姑漂亮,强逼我大姑做他的妻子。如果大姑不从,她的四个孩子也要像其他孩子一样,装在麻袋里打死扔进老母猪河。为了孩子,我的大姑屈辱地存活,后来饿死在一间破草房里。
花木丰富而神秘的情感,我们永远测不透。它们默默无声,超越了人类的感知,以特有的生命方式,表达着自己生离死别的感情。谁能想到,我家的石榴树,这棵目睹了大姑和姑父一见钟情的石榴树,竟然随大姑而去。石榴树年年都结很多籽粒饱满的甜石榴。我大姑出事前,树上挂满了石榴,一个个戴着艳红的石榴花。大姑遭遇不幸是麦收后,大姑回婆家没几天,没有风没有雨,我家的石榴在一个上午全都落果了。我的曾祖母看着东一个西一个滚得满地的小石榴,含着泪说:大女子出事了,大女子出事了!第二天,石榴树脱去它清翠的绿叶,光秃秃地站在阳光下。我爷爷剪断一根粗枝,流出的竟然是一股殷红的汁液。事后知道,这一天,正是我的大姑被逼迫的时候,而姑父在前线一无所知……亲爱的石榴树,它就这样为家人留下了苦痛的见证,伴随着我的大姑香消云散了!
令小山村所有人惊异的,还有禛婆家的柿子树。禛婆离世后,院子里那么高的一棵柿子树和我家的石榴树一样,叶落花谢,陪同祯婆和小富莉姑离开了这个惨无人道的世间!
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桂姨家的枣树,桂姨的丈夫是我祯婆的亲侄,他父母双亡,却留下了较丰厚的财产。他是跟着我禛爷奔赴前线打日本鬼子的。桂姨的娘家就在我们村的东街。桂姨家境一般,她新婚第三天回娘家,小两口带回一棵大枣树,栽在院墙东。为的是年年结枣添补父母的生活。这棵枣树还真争气,结的枣又红又大,老人吃不了,就到集上去卖。桂姨的丈夫参军前把桂姨送回娘家,叫她常住娘家,孝敬父母,养好孩子。临走时,咬着桂姨的耳朵说:你好好打理这棵枣树,叫它多结果!要是我回来没枣吃,我可得用棍打你!桂姨深知丈夫说的“打”蕴含着多少夫妻间的情爱,“我就盼他回来打我”几乎成了她在大姑家做军需时挂在嘴边的话。禛婆挨斗的那天,桂姨没在家,她带着孩子回婆家,说是趁好天把箱子、柜子的衣物都晒晒。当天晚上,桂姨的老爹大老远跑到桂姨婆家,告诉她禛婆的情况。桂姨是个刚烈聪明的人,她听说把禛爷说成特务,知道自己也逃不过他们的陷害,叫老爹领女儿回去,自己到别处躲躲。那帮强盗到桂姨老爹家翻箱倒柜,能拿的都拿走了,可桂姨再没有露面。
栀子花啊,请看看你们的历史,能找到桂姨的去处吗?她失踪了。那棵凝结着她和丈夫深情厚爱的枣树当年没有结枣,以后也再没有结枣。它挺立着,抖落了所有的绿叶,好像要向人们诉说着什么。秋去冬来,冬去春来。它再也没有泛绿,可它的刺却油亮坚实。人寰惨绝,慨世代之更变;天地有情,赐花木以殉贞。
花木通达明晰,秉承天意,向人类绽放,倾吐着爱的芬芳。死,以花魂陪伴,抚慰着被戕害屈死的生命。亲爱的栀子花,请代我谢谢你们众多的花木姐妹!
战争是对人的生死考验。不只是对前方的战士,也不只是对战士在后方的亲人,它也考验着存活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大地上的所有的人。抗日战争胜利了!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胜利”两个字在我眼前无限扩大。我看到流淌在字里行间的烈士的鲜血、战士的血汗和他们亲人不尽的泪水。这些为民族存亡流血流汗流泪的先辈是英雄,他们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甚至还遭到诬陷,但他们的精神光耀中华,他们永恒的生命筑起民族的丰碑。至于那些趁战火打劫谋取一己之利的东西,他们的灵魂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我妈妈目睹了她的三个会友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受非人的戕害,鲜活的生命含冤而去。她们美好的青春,她们希冀夫妻团聚共享天伦之乐的梦想,被彻底摧毁,付诸东流……
四个相濡以沫的妈妈,最后只留下我妈妈一人穿越了战争。然而,我年轻的妈妈怎么也不会料到,她含垢恩辱苦境熬磨十一年的守候,得到的是一纸离婚证书。
“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她没有争诉,没有反目,唯有默默找出22双精心绣织的鞋垫,每一双鞋垫都绣着洁白的栀子花,她亲手交给了那个曾经把她抱进了洞房的男人。
她把所有的苦水都吞咽在心里,她的哀愁只向青天诉说。妈妈有幸走进亘古长存的大爱,把人生看得那样淡定。我曾问起她的婚姻,她从未指责过对方一句。她只说,都健康地活着,就好。
汽车开到青岛东站收费站,下了高速路,便放慢了车速,不再风驰电掣般疾行。车速慢了,仿佛周边一切事物的节奏也都慢下来,缓慢的节奏渲染出这座海滨城市别具韵味的诗情画意。记忆突然拉下帷幕,我愣愣地呆坐在车里,看着路边缓缓闪过的风景。世界之光照耀着我回家的路,行道树举着绿叶浓密的伞盖,筛下斑驳的亮光,把林荫道点缀得光洁又美妙。最好看的是远处高楼的窗户,那些鳞次栉比的高楼墙上数不清的窗户,似乎全被亮光换成了纯金,灼灼金光把周边的树木映射得流光溢彩,返照着迷蒙的薄雾。沸腾的市声,绚烂的光华,让这个生气勃勃的城市展示出梦幻般的奇丽。
是谁放飞的一群鸽子,在街道的上空盘旋之后,背向大海的方向展翅而去。这些鸟儿啊,早晚会飞回它们生活的家园,这是大自然亘古以来赐给它们的智能。鸽子本来就是鸽子,1949年为拥护世界和平,毕加索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从此鸽子成为世人公认的和平象征,戴上了和平的冠冕,成为和平鸽。这足以见出人类对和平的向往。我的心也像放飞的鸽子,飞回我七十多年前的故乡,越过逶迤连绵的丘陵,盘旋在一片片起伏的黑色土地和嵌在其上的小小山村,见到了那些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她们梦寐以求的团聚似乎近在眼前,岂料瞬间全都破灭。我就像那只鸽子,衔着的橄榄枝去;返回时,橄榄枝浸透着栀子花那馥郁凄美而又无可挽回的哀恸。
在花木的日子里,所有的哀恸都是对今天的提醒。我分明听清了飘扬在栀子花芬芳里的优美旋律:
珍爱吧,不要悲恸!
珍爱家人,珍爱亲朋,
珍爱与你擦肩而过的人,
珍爱你没见过的所有人,
因为他们和你一样
拥有无比尊贵的生命!
栀子花啊,我永难忘怀的栀子花……
原载 青岛散文
责任编辑 高方
相关阅读 永恒的记忆——《栀子花香》创作谈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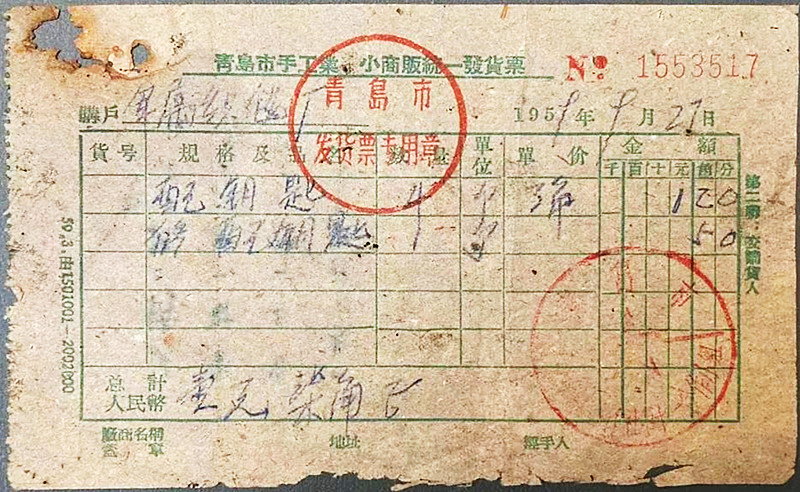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