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在乡下拍照,多次遇到完整的陶瓷器具,像碟子、海碗、酱坛子、咸菜缸之类,它们是如何走出百姓家门,经历了怎样的情节,最后如何保全自身的,我大都想不明白。也许因为想不明白,才看到了一些不普通甚至神奇的东西。
白庙子村东一条围子沟,一直延续到村北拐弯至村西头,村里老人说,从前村庄围子沟围了一个圈,围子沟里边是墙,也一个圈,坏人进不了村。现在只有过去的一半不到了,围墙全没了,只剩沟,挺深,四五米宽。没了围子沟的南边和西边,经常进坏人也说不定。不过,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不像过去那么好分辨了。我当然是好人,因为我是从村东中间位置下到的沟底,再往南。视线很南边,立着一棵大树,像榆树,荫下一座小桥,东西横在沟上,这一树一沟一桥成景,也像好人,说不定还有年头了。于是我顺着大沟朝南走,步伐很轻,十分小心。
离小桥不足三十米处,我遇到那只碟子,很完整的一只菜碟子,当然也可以盛卷子馒头,正面朝上躺在沟底,全白色,三朵花枝均匀地分布在碟子边沿。花枝也是农村田野常见的,朴素的喇叭花,也可理解为指甲花。每朵的花枝用绿色,花朵一阴一阳,阴的绿色勾边,阳的施以粉紫,整体素淡,还算雅致吧,盛上一盘土豆烩芸豆,点几片芫荽叶子,保管叫人胃口大开,不用劝,我必大吃一顿的。现在,它盛了半碟子干枯的杨树叶,自然是不能吃的,不过,它目前的状态告诉我,对它来说,人世间的繁华早已不值一碟。
我走路很当心,没踩到它,蹲在它跟前拍下一张照片,随后费力思考它如何完整地从村庄到这条沟的南头来的。我习惯思考那些看上去用不着思考的东西,就是思考秃子头上为什么生虱子,开会时那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为何一直说他想做点好事等等,所以额头有很深的川字沟,比村庄只有一条沟厉害多了。我朝白庙子望望,直线距离不会低于三百米,离其他村庄更远,无疑它应该是从白庙子出来的,可是无疑往往存疑,理直气壮的嘴总是连着花花肠子。也许它来自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那我可发财了,不对,那时候人眼还没进化到识别颜色,只会做黑陶。唐三彩?白、绿、紫三色没错,没办法了,也得发财。但是它仰面躺着,并不避嫌,不怕被人带走的意思,应该不值钱。我找到了理由,书上说慎独,君子不掠地之美,我不能带它走,咬牙跺脚朝小桥而去。后来把肠子悔青了,因为我可能错过了发财的机会。现在,说不定它还躺那儿,我遇到它是 2018 年11 月份。
最近我思考明白了,碟子去沟南无非为了更加真实的生活,寻找过去的自己,比如一捧黄土,比如树叶在它体内脱水的过程,比如为了见到在炕头不允许它见到的风雨。
然而,从室内到大沟这三百六十五路,它怎么保全自己的呢?
23
五龙河的终点在槐家村东北不到二里路入胶莱运河的地方,2018 年 3 月初我到过这里,顺便进了槐家村四处走走。村庄不大,在村中间东西方向上有条大沟,是五龙河流淌百里路上最后的支流。大沟又深又宽,名副其实的大,体型上感觉超过五龙河。沟上一座砖石桥,桥面与村庄的南北主路齐平,铺设了水泥,从桥头面朝北,就见路东沟沿上五间房子,被枯干的杂草和没发芽的树丛包围。别人也许不在意,我特别在意,因为它被完全废弃了。
院子的三面围墙都倒塌了,门楼还在,孤零零的,很完整,四个边角镶着大青砖,顶挂红瓦,门槛铺设厚重的青石条,很气派。五间房子双坡都铺红瓦,屋脊使用燕尾瓦盖住,西山为悬山式,东山为硬山式,也许从前东山紧挨邻居房屋的缘故。山墙用的是土墼一层层叠加上去的。土墼在预制过程中,由于添加了大量的麦糠而特别结实,耐雨水侵蚀。五间房的门窗都封堵了,进不去,我在院里转悠了一会儿,没什么特别要记住的,便从院里直接下沟里去。沟的半腰立着一棵特别粗壮高大的青杨,我想去看看。
枯草太厚,我滑倒了,屁股着地,快速举高相机往下滑,很快到了青杨树下,还好一个小平台,我趁着下滑的力站在了平台上。青杨有我两个粗,仰望也无法瞧见树梢,我冲它竖了竖大拇指,再看树底下,好像有东西。相机放进背包,扒开树叶,前些年的叶子腐烂了,十几厘米厚。烂叶下面,先掏出一个海碗,又扒,又掏出一个海碗,再扒,没有了,下面是硬硬的黄土。
两个海碗是粗瓷烧制,颜色发黄,里里外外都是小雀斑。我小时候,一直到二十岁前,大约一九八五年以前,都用这种海碗吃饭、喝水,搞不好还端着它讨过饭,对它十分熟悉,立刻一肚子亲切感,不是从油里生出来的,小时候吃糠咽菜,肚里没油。肚里有油的不用这种黎民用的粗瓷,他们都用“康熙御制”和“乾隆御制”的细瓷,比如像今天有的人专抽细烟,专喝酱香。我盯着两个海碗,一是琢磨拿它们怎么办,二是思考它们怎么来的树下,还刻意掩埋起来。带走是肯定的,发财的机会岂能错失?我望望上天,再看看那趟老房子,一个情结油然而生。
女史,就是老房子的女主人,一大早掀开躺在床上男史的被窝:
“死鬼,把那两个破碗扔掉,要搬的东西太多,实在放不下了。”
男史不情愿地起床,皱着眉头,一脸不高兴,左手提着裤子,右手从锅台拿起两个海碗跳到天井,看看院南墙,一弯腰,右手可就使上劲了:
“出去吧,您。”
海碗“嗖——”一家伙飞了出去,又高又飘,几乎够到了青杨树梢,就见它们半空中连续二十几个托马斯全旋,然后猛然静止,定住,朗声道:
“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
说毕,一声爆炸,两个海碗碎为齑粉。女史听见响声,感觉不对付,抓起供桌上的笤帚,跑出当屋门:
“死鬼,让你扔破碗,怎么把好地扔了?”
2025 年 1 月 14 日
阿龙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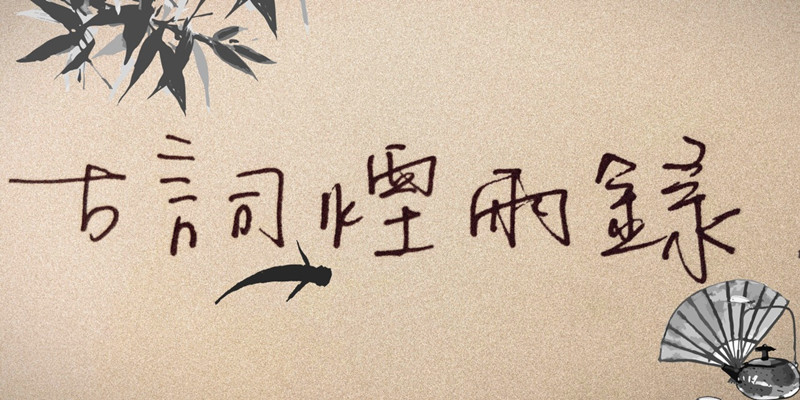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