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身到书橱取书
无意识望向窗外
哇塞
地上不知何时已经落满厚厚的积雪
此时,脑海中便突然浮现出白居易的诗
于是火速回到书桌伏案疾书:
孤灯相映红宣纸,
不知不觉间墨干纸亦尽。
夜深鸟儿都打鼾,
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于是起身欲打开书橱拿出诗书读。
突然发现窗外不知何时已经有了厚厚的大雪……
于是,心底深处突然冒出一诗句:
红泥小火炉。
也突忆起白居士,
屈指算来,白居易前辈已故1179年了。
在这万籁俱寂白雪覆盖的世界,
应该有一个随时随地在身边陪伴并倾诉的人,
只是这最基本的人间烟火气,
我却不知道在这大千世界里,
应该到何处觅。
罢罢罢,
欲将心事付与雪和月,
只有窗外的知音在漫天飞舞,
而亘古不变,
天地日月星辰都一齐不开口。
走到室外,
脚下是一尘不染的雪地,
我望而却步,
不想破坏这一尘不染的世界。
于是,对天吟诵最应景的诗句: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今晨周末按照惯例睡到自然醒。
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侧门进入后花园。
后花园并不是很大,
种植的植物无非是竹子、云锦杜鹃、鹅掌柴……
还有最大的一棵树。
其实,诗社前院种植的一棵高松树、一棵矮的柏树是诗社的主角
因为到诗社的人都必须走前门(正门)穿过这两棵树。
也许是诗书读得多的缘故,
看到竹子松柏,就随即想到: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突然,
天空中传来鸟的叫声,
我潜意识地抬头仰望,
不知何故,
脚下滑了一跤,
我倒在雪地上并没有感觉摔得疼,
却发现雪地上我留下的脚印美轮美奂,
散发着自由、淘气和傲慢的张力……
是的,
你可留意雪地里踩下一串串洁白的脚印,
你可在摔跤的时候记录生活的支离破碎的真相。
对于上苍赠予一场场圣洁的雪,
我是有特殊感情的。
蓦然回首,
流着鼻涕的儿时,
背着书包踏着洁白的雪,
匆匆忙忙地走在上学与回家的路上;
少年,
踏着洁白的雪,
骑着自行车,慌里慌张地奔波在学校与回家的路上;
长大工作以后,
为了生计,
开车奔驰在一望无际的雪海公路……
当经济条件宽裕的而立之年,
因为喜欢读书,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2004年春,
我齐东路创设“诺贝公益读书阁”。
每当冬日下雪时,
我就有了闲情逸致,
弃车步行过一段漫时光。
从福山路11号穿过青岛海洋大学的南门,
绕行西门到齐东路6号诺贝读书阁。
我个人认为,
那时雪地里留下的脚印,
应该是最诗情画意的一行……
而这一切都定格在2004年春至2008年春,
当然,
这就是我在中国感受到最大的幸福指数了。
思绪是扯远了,
然而一路走来,
这曲曲折折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厚重不一的脚印,
的确都是在雪后的路上体现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
雪还是天空中下的雪,
而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地点、时间和地点感受就不一样了呢?
三日前,
我第七次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回来以后,
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身份,
不是说,
人人生而平等,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吗?
为什么?
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不同的家庭环境,
人和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生就有了天壤之别呢!?
不是说,
上苍不会把所有的好事都给一个人,
同样,也不会把所有的坏事都给一个人,
到底后天的努力管不管用?
到底天生我材必有用是在什么环境下管用?
为什么?
全世界人的笑声、哭声、愤怒声、生死都是相通的,
然而,
人的思想意识认知和所处的地域不同,
便有了那么多条条框框以及束缚制约呢?
此前,
看到过最露骨和直白的话,
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砝码太低;
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经受的诱惑不够大。
我不知道,
这是写给大多人的心态,
还是全部人的内心世界。
我不喜欢争辩,
我没有信仰,
我只是遵从内心的声音,
我摔倒了,会一个人爬起来。
此时,
我脚下这片土地,
这里的人是可以肆无忌惮地大骂总统而无任何罪名的。
当然,
你可以骂当权者,但是你不可以欺辱弱势群体,
更不可以有种族歧视,
在这里对于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员,
在这里的法律是倾向保护弱者的,
当然在这里弱者可以受到足够的尊重。
在此,
感恩雪地里留下的这串脚印,
它给我太多的思索和感慨……
生而为人,
同在一个地球,
每个人生存仅需要的空气、水、食物而已,
为什么?
生在国度制度不同,
就一定会有不同的人生,
就有了不同的幸福指数。
这里,
我始终相信,
历史的车轮始终是滚滚向前迈进的,
最终人们的观念里不再会有国与国的地域观点,
哪里自由就到哪里去,
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阻挡得了。
是的,
在不久的将来,人人都会诞生在自由法治民主的环境下……
此时,
我站在“纽约一心禅诗社”牌匾前,
点燃人人生而平等的火把,
伴着火苗中照亮的诗行。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诗集;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盏诗意盎然的明灯。
是的,
真正照亮黑夜的不是太阳,
而是内心的诗火、
眼中的诗光。
只是,
你一定要做那个追光的人。
雪地的脚印,
我灵魂的追随者,
人世间,
知我者,
一二一,
足矣!
2025年月9日于纽约一心禅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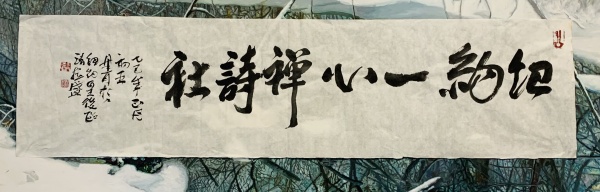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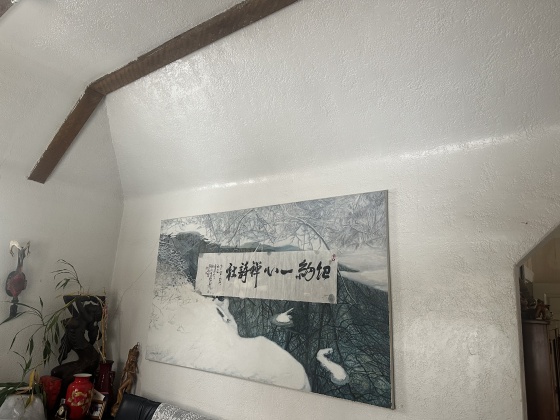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