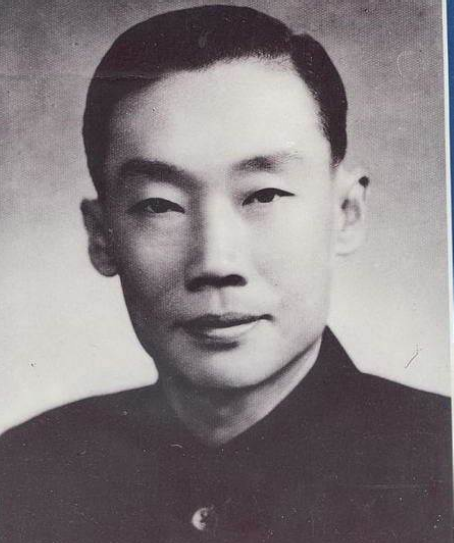陈浩武教授的解答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他对宗教改革的解读、是大家都知道的流行说法,并无新东西。陈浩武教授虽然谈到“龙场顿悟与宗教改革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不是个差异的问题,把两者扯到一起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陈教授对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也作答,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我们不感兴趣王阳明的龙场顿悟。很想听听您对宗教改革的看法,您毕竟是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时下中国持续十多年的“弘扬”,国学家鼓噪孔孟之道的话说得够多了,继续“弘扬”,已感到囊中羞涩,“弘扬”下去无话可说了。于是不甘寂寞的国学家又拿王阳明说事。一时间里谈王阳明心学的文章纷至沓来。把王阳明捧上了天。并将王阳明的龙场顿悟与欧洲的宗教改革相提并论。其实“相提并论”没有道理:两者既无类同之处,也无相似之点。都知道宗教改革推动了欧洲的历史进步与社会发展。但是王阳明龙场顿悟后的中国却重蹈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旧辙将近四百年……
文友让我谈谈宗教改革,是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不过文友所说的“王阳明后的中国重蹈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旧辙将近四百年”,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符合:
王阳明后到满清王朝垮台,是三百八十年。在这三百八十年里,中国并非一直推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国策。始于明朝隆庆皇帝的晚明“文治响盛”时期,开放海禁、对外开放、国际贸易大发展将近七十年。
明朝嘉靖皇帝剿倭几十年,造成国库空虚,国力衰退的局面。隆庆皇帝登基后,国家财政连朝廷的正常开支都不能维持。于是隆庆皇帝不得不违背祖训,开放海禁,允许民间从事国际贸易活动。朝廷从中收取关税解决财政困难。
开放海禁带来了晚明国际贸易如火如荼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繁荣。促进了江南一带工商业、种植业全面繁荣与发展。
半个多世纪的对外贸易一直是顺差!世界每年白银总产量有将近一半通过贸易流入到中国来了。晚明的对外贸易既创造了国际贸易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又创造了晚明“文治响盛”的繁荣与昌盛。所以有学者说:
“文治响盛”是两千多年农业文明中国升起的第一道商品经济曙光!中华民族在晚明出现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遗憾的是,这个希望不久破灭在满清入关的屠刀下。
需要特地指出的是:晚明国际贸易带来的“文治响盛”都是晚明人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到东南沿海一带,从事地下走私活动,在隆庆皇帝开放海禁后,这些走私活动摇身一变,成了公开的国际贸易。
晚明经济发展的全部奥秘是:人人都有的致富欲望,才是创造晚明“文治响盛”的唯一力量源泉。与王阳明的龙场顿悟没有半点关系。
不知为什么,晚明的“文治响盛”这段历史在教科书上竟然阙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的力作《晚明史》。下面谈谈欧洲的宗教改革。
学界对宗教改革的通常说法是:1517年德国神父马丁•路德以批判罗马教廷的救赎卷为主题的《九十五条论纲》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后来加尔文推出的《基督教要义》阐述的五大要点,将宗教改革具体化为思想行动。
由马丁•路德、加尔文在读经中形成的新教认为:
通过圣经聆听上帝的声音才明白了:人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上帝的选民。只有绝对地相信上帝的恩赐,人们在实现以信称义中才能得到救赎。一个虔信的信徒必须像上帝的选民那样体面地活着,用自己的努力奋斗、艰苦创业实现致富的目标。实现致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更重要的是再投资发展工商业,以事业上的成功荣耀上帝。这才是世俗人活在信仰意义上的伟大目的。
新教的这个伦理思想激发人们纷纷涌往市场。于是欧洲人被禁欲主义压抑了千年之久的致富欲望,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欧洲的市场经济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欧洲各行各业的兴旺与繁荣。地理大发现,又使欧洲的市场经济走向全球化。从而加快了欧洲近代化的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国王断然地夺回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所有权力,割断了英国教会与罗马教廷的联系。没收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所有财产。改造英国的宗教成为国教,教会应该为国教服务,不再是罗马教廷的附庸。
亨利八世围绕宗教推行的各项改造,积极地呼应了欧洲大陆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成为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有力地唤醒了英国人在罗马教廷统治时期被压抑了的思想,思想解放了的英国人开始积极投入为致富而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潮流中。人们争先恐后地从事工商业活动,力争通过自己艰苦创业取得事业的成功荣耀上帝。
如果说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了欧洲的近代化;那么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则把欧洲的近代化推上了充满希望的快车道。这个快车道就是市场经济的大发展。
然而欧洲近代化中的市场经济之路,却被十九世纪西欧那帮空想主义思想家上纲上线为: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反对罗马教皇统治中开辟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如上所述,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伦理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人类天生的致富欲望名正言顺地付诸社会实践,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宗教改革后的欧洲人创造的社会发展新气象,都是源于市场微观上出现的经济活动,哪来的什么资产阶级引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人人在致富实践中形成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民间自发现象,怎么就变成了骇人听闻的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那些引领市场繁荣与发展的企业家怎么就成了原罪的资本家?企业家都是繁荣社会、发展社会的精英,怎么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中成了有罪的敌人?
全部的人类近代史彰显一个朴素的道理:在近现代化的路上,在人类追求富裕的社会实践中,还有什么比轻贱、仇视企业家更愚蠢的呢?
需要指出的是:有太多谈宗教改革的文章都忽视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
宗教改革并非在一个早上被马丁•路德用一纸讨伐罗马教廷的檄文就掀起了波及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实际上,远在马丁•路德、加尔文之前好多年,包括很多神父在内的欧洲人,已经开始对罗马教廷的囤积财富、占有大量土地、生活奢侈、发放救赎卷、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严禁思想自由等做法极为不满。不少神父公开批判了罗马教廷。像布拉格大学校长兼主教胡斯、意大利神学家萨沃纳罗拉,他们因为批判罗马教廷而被教皇处以火刑。
实际上十六世纪初叶出现的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中世纪欧洲长期积累的对罗马教廷不满情绪的总爆发,是欧洲人精神长期遭受压抑的思想起义!
但是有文章认为:宗教改革推进了欧洲近代化的实现是摆在那里的常识。不过宗教改革削弱了罗马教廷的权威、限制了罗马教廷权力,罗马教廷失去了对欧洲人思想的“一统天下”,罗马教廷对欧洲人的思想垄断便不复存在了。于是很多教派教会自立门户自成一家。他们在缺乏相互沟通中,因为地缘政治的分歧出现了势不两立的对抗,终于酿成了残酷混战的三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给欧洲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损失。如果没有宗教改革,则不会发生三十年战争。
这个说法是事实,也有道理。但是若无宗教改革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使欧洲人在勃发致富欲望中纷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则不会有欧洲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没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欧洲的近代化恐怕有天无日头。没有欧洲近代化的成功,则不可能有欧洲的现代文明。没有欧洲的现代文明,则不会有人类的现代文明。
实际上,欧洲近现代化中创造的现代文明,是对全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
非议宗教改革的人没有看出:只有削弱了罗马教廷的权威、限制了罗马教廷的权力、终止了罗马教廷不乏中央集权性质的“一统天下”,才出现了欧洲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谁见过集权统治的国家出现过市场经济?
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欧洲能有近代化的成功吗?能有欧洲的现代文明吗?能有人类的现代文明吗?
当然作为宗教改革的带头人马丁•路德、加尔文、亨利八世,搞宗教改革不一定有发展欧洲市场经济的战略眼光。但是他们推动的宗教改革解放了欧洲人思想,摆脱罗马教廷对欧洲人的思想禁锢,所以才有了欧洲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唯其这个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才是欧洲近代化成功不可缺的重要条件。
非议宗教改革的作者没有看到,宗教改革终止了罗马教廷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对欧洲人的思想解放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非议宗教改革的人没有看出,罗马教廷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让所有的人都听从罗马教廷借圣经发出的指示,这种做法的实质是禁锢了欧洲人的思想,剥夺了欧洲人的思想自由——这才是欧洲在中世纪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所以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教廷对欧洲人在思想上的“一统天下”,具有深远意义:
欧洲与中国在晚清时期的国土面积大致相当。如果没有宗教改革,欧洲继续在罗马教廷的中央集权意义上的“一统天下”,欧洲会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吗?欧洲会有今天的先进、发达、繁荣、富强吗?
反证的道理是:中国若不是秦统一六国推行皇权中央集权制,若不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会蹒跚在农业文明社会里两千多年停滞不前?
中央集权制与“大一统”的严重后果是压抑了人的天性欲望,杜绝了思想自由,窒息了社会生机,中国失去了进步与发展的动力。
所以宗教改革动摇了罗马教廷在思想上“一统天下”欧洲的根基,打破了各国既听从罗马教廷的思想指示、又按照罗马教廷的思想要求行事这种荒唐的做法,是宗教改革的思想亮点。唯其这个思想亮点才唤醒了欧洲人被压抑了千年之久的自由意志。
三十年战争固然是欧洲的一场灾难;但是没有三十年战争,则不会有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众所周知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划时代意义是,世界从此有了现代文明的国家;世界各国有了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难道不是吗?《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后的欧洲进入了将近三百年的“洒满阳光、开满鲜花”的国泰民安时期。
所以谈宗教改革 ,不必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写成一部洋洋洒洒的大书,高谈阔论子虚乌有的资本主义精神。欧洲人的致富欲望在市场上风生水起,人们忙于挣钱、发财致富,虔诚于以事业成功荣耀上帝,哪来的什么资本主义精神?
宗教改革解放了欧洲人的思想,释放了上帝赋予人的致富欲望,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天性欲望的付诸实践,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呢?
所以谈宗教改革,应该着眼于上述思想解放中的欧洲人,他们的“致富欲望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这才是推动欧洲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才是欧洲近代化进入快车道的根本原因。
唯其欧洲人的致富欲望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宗教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离开欧洲近代化中市场经济大发展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谈宗教改革,都是不着肯綮的多余话。
诚然,欧洲近代化的成功是以市场经济大发展为条件的。虽然市场经济发展与宗教改革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市场经济发展却与思想解放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思想解放却是宗教改革的逻辑结果!
于是,“宗教改革带来了欧洲近代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这个论断便拥有了所向披靡的逻辑力量!
这个一看就明白的欧洲近代化中的基本常识,却淹没在十九世纪西欧那帮思想家杜撰的“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天方夜谭中。
二十世纪的东方学界推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时间,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欧洲近代化的经典思想。这个经典思想的流行,使上述“思想解放中欧洲人勃发的致富欲望,推动了市场经济发展这个再简单不过的基本常识”被冷落到无人问津角落里去了。
人们谈重大历史事件,总是愿意避开常识作宏大叙事,从中演绎出并不反映历史事件本质的长篇大论。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宗教改革最本质的要点是,在批判权威中夺回了原本属于个人的思想自由。
但是宗教改革不是从上而下发动的体现国家意志的运动;也不是社会底层人发起的群众运动。而是几个拿着教会俸禄的体制内人,出于良知、出于正义、出于对信仰的绝对虔信,冒险批判罗马教廷的“登高一呼”。从而获得了欧洲人的积极响应与坚决支持,遂成思想解放运动。
可以肯定地说,若无马丁•路德、加尔文、亨利八世等人的英勇无畏的“登高一呼”与引领,则不可能有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那样的话,欧洲近现代史、人类近现代史,就不是我们知道的模样了。
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历史假设的逻辑是存在的!这个逻辑让十九世纪西欧空想主义思想家提出的“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这个著名论断,在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面前苍白无力了!
马丁•路德、加尔文肯定知道先他们之前的那几个批判罗马教廷的神父,都牺牲在罗马教廷的火刑中。
所以发起并推动宗教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几个带头人,不仅有思想、有见识、有正义感,还有出于维护神圣信仰的绝对权威与崇高意义才有的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