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浪声沉),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孙吴)赤壁。乱石穿空(崩云),惊涛拍(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应是,笑我早生华发)。人生(间、间如寄)如梦,一尊(樽)还(远)酹江月。
在这九个版本之外,周策纵先生在其《废园诗话》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
大江东去,浪声沉、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一版本除了个别字的差异,最大的出入在于其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一句上,周策纵版将这一句如此断句:“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关于《念奴娇》词牌,因苏轼“赤壁怀古”词有“大江东去,一樽还酹江月”句,因名《大江东去》,又名《酹江月》《赤壁词》《酹月》。曾觌词名《壶中天慢》。戴复古词有“大江西上”句,名《大江西上曲》。姚述尧词有“太平无事,欢娱时节”句,名《太平欢》。韩淲词有“年年眉寿,坐对南枝”句,名《寿南枝》,又名《古梅曲》。姜夔词名《湘月》,自注“即《念奴娇》,鬲指声。”张辑词有“柳花淮甸春冷”句,名《淮甸春》。米友仁词名《白雪词》。张翥词名《百字令》,又名《百字谣》。丘长春词名《无俗念》。游文仲词名《千秋岁》。《翰墨全书》词名《庆长春》,又名《杏花天》。《碧鸡漫志》云“大石调,又转入道调宫,又转入高宫大石调”,姜夔词注“双调”。元高拭词注“大石调,又大吕调”。此调有平韵、仄韵二体,《钦谱》以为,此调仄韵词以此词为正体。
苏轼平生写过两阙《念奴娇》词牌的词,都写于元丰五年(1082),一阙是写于此年七月的《赤壁怀古》,另一阙是八月十五写的《中秋》,两阕词均是双调一百字,押仄韵。因为一个“了”的归属,钦谱将两阕词中的《赤壁怀古》定为一格。
《念奴娇·赤壁怀古》 双调一百字,前段九句四仄韵,后段十句四仄韵: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寄,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中秋》双调一百字,前后段各十句、四仄韵:
凭空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幡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可见苏轼对于《念奴娇》正格并不陌生,两阕词写作时间差了一个月左右,为什么后一阙完全遵守正格,而前一阙却自创“新格”?是苏轼有意为之,还是后人想当然耳?《容斋随笔》载此词云:“大江东去,浪声沈、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孙吴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词综》云:“他本‘浪声沈’作‘浪淘尽’,与调未协。‘孙吴’作‘周郎’,犯下‘公瑾’。‘崩云’作‘穿空’,‘掠岸’作‘拍岸’,又‘多情应是、笑我生华发’作‘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益非。而‘小乔初嫁’宜绝句,以‘了’字属下句乃合。” 《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是南渡词家,距离苏轼的时代不远,又本黄庭坚(鲁直)手书,必非讹托。《词综》所论,最为谛当,周策纵先生论述的依据也是本于此,周先生还对自己能搜罗到的《念奴娇》词牌的所有词作进行分类分析,进一步确定“了”应断在下句。与周策纵先生持同一观点的还有吴世昌先生。显然,围绕“了”字的断句问题,学界是存在分歧的。这一断句之争不仅涉及语法与韵律的辨析,更关乎对词意内涵与苏轼创作意图的深层理解。
对于周策纵和吴世昌两位先生所主张的断句,此处分析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新断句的合理性是否成立?二,是否存在周策纵先生认为的苏轼词作深受柳永影响,进而影响其词句结构?
周策纵在《苏轼〈念奴娇〉赤壁词格律与原文试考》(见《弃园诗话》)一文中,围绕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断句问题,提出两点关键主张:首先依《念奴娇》正格,词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应断为“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并认为这是更符合词牌格律的读法。其次从词风溯源角度,周策纵认为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深受柳永影响,他列举苏词《鹧鸪天》末句套用柳永《雨霖铃》句法,并且指出《念奴娇》的“大江东去”与柳永《双声子》的“晚天萧索”存在创作关联。
其次,周策纵特别强调苏轼受“柳词影响”,他从苏轼赤壁词用词的渊源问题入手,他认为此词很受了柳永《双声子》一词的极大影响。这点好像还未受到前人注意。为了对照方便,且录柳词全文如下: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三吴风景,姑苏台樹,毕落暮霭初收。夫差旧国,香径设、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
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周先生在文中分析:“首先,我们该注意,这首词和赤壁词的主题相似,都是登临怀古之作。柳词是记作者游姑苏,想起古时吴、越之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争霸,中间夹杂有范蠡和西施英雄与美人的故事,但时代过后,都成往迹。苏词如大家熟悉的,记作者游黄州赤壁,想起古时吴、魏之战,孙权、刘备抵抗曹操的南征,中间也夹杂有周瑜(公瑾、周郎)和小乔英雄与美人的故事,而时代过后,也风流云散了。吴、越与吴、魏虽然不同,但都有‘吴’国。二词所怀念的史实既然类似,而感叹时间终于消磨了英雄美人、风流人物,这种吊古的悲情,更是相同。”周策纵进一步论及:“事实上,除了作者和来源颇成疑问的李白《忆秦娥》之外,柳永的《双声子》也许是最早的登临怀古词作。以后才有王安石(1021—1086)的《桂枝香》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显然,从题材上的承继关系上看,苏词有明显地对柳词的追慕。“对比一下柳词和苏词的用词与意象。最明显的当然是苏词完全袭用了柳词那句‘江山如画’。苏轼大约很喜欢这句的形象,所以在一个多月后在另一首咏中秋的《念奴娇》里,再用了这一句。……试看柳词描写,‘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繁范蠡扁舟’苏词对江山的描绘,次序略有颠倒。柳是先出江山,再加描写;苏则先加描写,再说江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二词末了一句都在表示江山如此,而英雄人物不存。‘翻输’句是反衬吴越称王者皆消亡;‘一时多少’句也是用反问句来表示豪杰无存。……我说柳词‘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的‘云涛烟浪’也影响了苏轼赤壁词,这从苏轼另一首《念奴娇》咏中秋词也可见到类似的影响。此词上片末二句说:‘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也接着用了‘烟’字。”周策纵先生认定赤壁词受了柳永词的影响,但并不是说柳、苏词的风格全同。“我个人认为他们二人有同有异,各有其独自的风格。不过我想强调的有两点:一是我认为苏对柳词,素多重视与喜好,并无鄙薄之意。传说他对秦观说过:‘公却学柳七作词’其实这只是给秦观风趣的赞词,后人往往误会夸大,以是对柳永词有轻视。其次,苏轼对柳词非常熟悉,他对秦观说的‘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非熟悉柳词者决道不出。”叶梦得《避暑录话》里说:“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赏,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病,故尝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周策纵对此另有一番发挥:“其实所谓‘以气格为病’,只是叶梦得的看法,苏轼那两句‘戏云’,只见赞叹,未见是讥评。柳词《破阵子》正列在柳集我上文所引《双声子》词之前。大约这两词都受到苏轼特别注意过。”为了进一步证明苏轼欣赏柳词,周策纵又举出宋赵令峙《侯鲭录》的例证,“苏轼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当然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以此为晁补之语,但周策纵强调晁补之少时即受知于东坡,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是此语源于苏,仍有可能。因此苏轼虽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自诩“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但其创作中不乏对柳词的隐性吸收,周策纵认为,苏轼对柳永的态度是“批判性继承”,既否定其俚俗,又吸收其长调结构与铺叙技巧。
吴世昌先生同样坚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断句(见《唐宋词概说》),并且提出新解,认为“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中的“了”可以解读为副词“全”“全然”或“极其”,而非句末助词。这一观点旨在说明苏轼并非不守格律,而是后人断句错误导致误解。 他为这一观点举出两例佐证:一是秦观《好事近·梦中作》:“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此处“了”修饰“不知”,意为“全然不知”,无人质疑其格律问题。二是韩偓《宫柳》诗:“幸当玉辇经过处,了怕金风浩荡时。”《汉语大词典》释此“了”为“极其”“非常”,强调程度之深。在古汉语中,“了”作副词时, 多置于动词或形容词前,如“了无惧色”“了不可见”。但亦有例外,如韩偓诗“了怕金风”,其用法与苏轼“了雄姿英发”相似,均以“了+形容词”结构表程度。结合这阙《念奴娇》,若“了”解作“全然”,则“了雄姿英发”意为“全然英姿勃发”,强调周瑜新婚之际意气风发的完整状态,与后文“羽扇纶巾谈笑处”形成呼应。另外一个事实,周瑜纳小乔发生于建安三年(198),而赤壁之战在建安十三年(208),两者相隔十年,故“初嫁”与“雄姿英发”未必同时。若断为“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可暗示婚姻为周瑜后续成就的铺垫。当然苏轼此词并非严格写实,而是借历史符号抒怀,时间细节的错位恰是文学想象的体现,未必需要机械对应,但可聊备一说。
关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小乔初嫁了”的断句之争,实为古典文学文本阐释的经典案例。这场争论触及词学研究的三个核心维度:一、格律与文本的辩证关系。《念奴娇》正格要求下片第三句为四字句,周策纵据此主张“小乔初嫁”四字成句有其依据。但同时应该看到,苏轼此词前片“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已用三、六句式,可见其突破定格之倾向。词谱演变史显示,自东坡此作后,“大江东去”体遂成新格,这恰是词体在天才作家笔下获得新生的明证。正如万树《词律》所云:“东坡此词为《念奴娇》变格之祖,后人自当遵用。”二、语法与诗意的双重校验。吴世昌先生提出“了”作程度副词的新解,在训诂学层面确有依据。然细审全词语境,“初嫁了”构成的时间链条与后文“谈笑间”形成精妙呼应——前者定格人生重要时刻,后者展现决胜瞬间,共同塑造周瑜“少年英雄”的立体形象。若作“了雄姿英发”,虽副词用法可通,却割裂了婚姻节点与英发状态的因果关系。正如王国维所言:“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此处文脉的贯通更胜于孤立字词的考辨。三、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周策纵揭示的柳苏词脉关联颇具洞见。柳永《双声子》的“江山如画”确为苏词所本,但苏轼实现了三重超越:将柳词的铺叙转化为意象并置,将平面化历史感叹升华为生命哲思,将市井化的语言提炼为诗性表达。这种转化在“小乔初嫁了”"的句式中得以彰显——通过日常口语“了”字的诗化运用,既保留柳词的世俗鲜活,又注入士大夫的典雅气质,恰如钱锺书所言:“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的转型缩影。
关于“了”字和《大江东去》的断句之争给当下带来阐释学的现代启示,这场争论映射出古典文本阐释的永恒困境:当文献考据、格律规范与审美直觉产生矛盾时,何处寻求平衡点?周、吴二先生的质疑虽未颠覆传统断句,却开辟了新的阐释空间。如接受“了雄姿”的解读,可引发对英雄成长轨迹的重新审视——婚姻或是周瑜从少年将领蜕变为军事统帅的关键仪式。这种现代视角的投射,恰印证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理论,使千年文本持续焕发新意。而“了”作为句末助词,表动作完成,则符合古汉语的常见用法,“了”用于句末,表示时间流逝的瞬间性。“初嫁了”意在强调周瑜与小乔新婚之际的意气风发,三字简洁凝练,既点明婚姻的新鲜感,又为后文“雄姿英发”蓄势。从结构上看,“小乔初嫁了”与“雄姿英发”形成语义递进:前句以婚姻象征周瑜人生阶段的圆满,后句则聚焦其外在英姿与内在才华的完美结合。二者共同构成对周瑜“少年得志”的立体刻画。这已成为一般共识。周、吴两位先生的新解虽具启发意义,却因语法牵强与语境脱节,恐怕很难以撼动传统断句的合理性。当然不能完全忽视周、吴等人的断句体现出来的现代阐释学的“文本开放”理念,他们主张将“了”置于句首,虽语法存疑,却可能引发对周瑜形象的新思考:婚姻是否是其英雄气概的“完成仪式”?这种解读带有现代人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投射,通过重新解读激活经典的多重意蕴。然而,学术争鸣的价值不在于定于一尊,而在于拓展解读的维度。周策纵、吴世昌两位先生的尝试提醒我们:经典文本的意义并非封闭,而是随时代语境不断生长。或许正如苏轼笔下“大江东去”的奔流,文学阐释亦应在坚守文本根基的同时,拥抱多元的浪花。
一个“了”字,两种断句,浓缩了词史演进的微观样本,彰显了苏轼此词在词史上的特殊地位,一阕词的任何细节改动都牵动文体演进脉络。若从定格角度苛责“小乔初嫁了”不合律,则遮蔽了词体突破的重要节点。宋翔凤《乐府余论》早有论断:“东坡以横放杰出之才,遂为词家别开生面。”这个“了”字的安放,恰似词体解放的宣言——将琐碎的生活细节升华为宏大的历史悲慨,实现了词从“缘情”到“言志”的功能转变。即使承认其为“变格”,也必须承认这是苏轼对词格的一种贡献。
概而言之,这场断句之争的本质,是词学研究方法论的三重对话:校勘学与文艺学的对话,传统笺注与现代阐释的对话,文体规范与创作自由的对话。苏轼词作最终呈现的开放性,恰是中国古典文学强大生命力的体现——正如滔滔江水,在既定的河床中奔腾出万千气象。
修改于2025年2月19日
原载 读曰乐
2025年2月19日 08:35 青岛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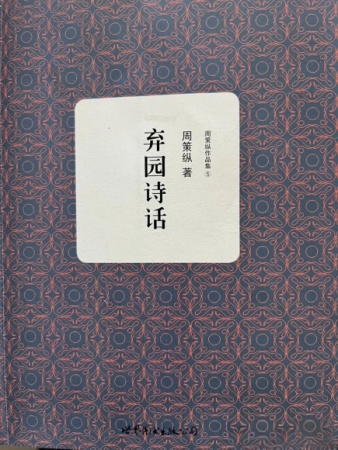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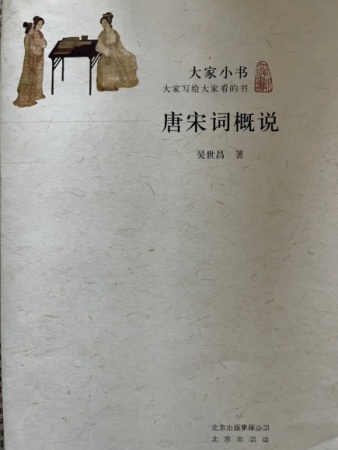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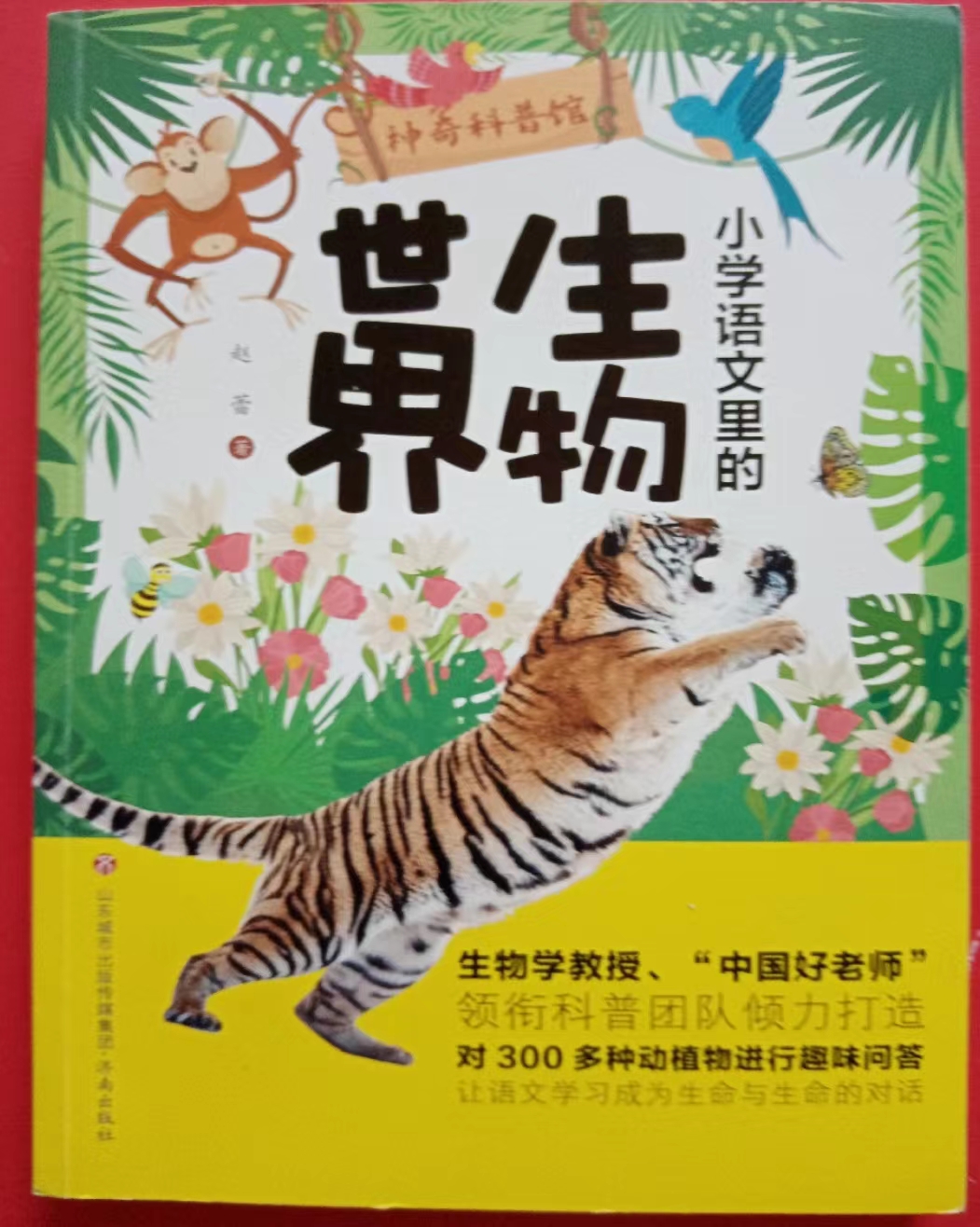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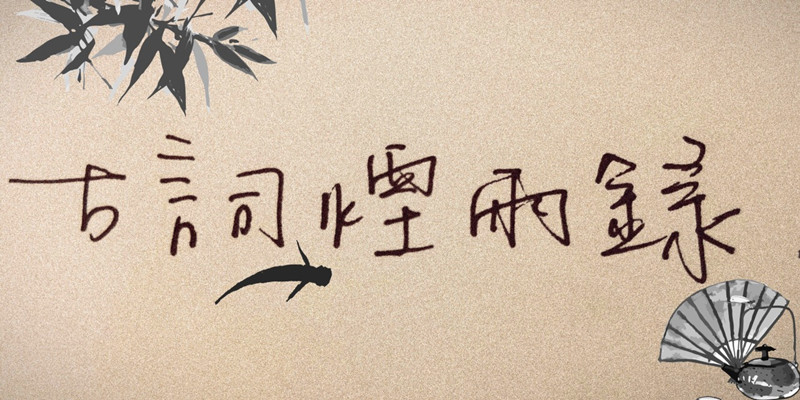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