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问刘十九》(唐·白居易)
特别喜欢这首诗,总觉得白居易是一个很性情的人,无论他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还是把诗歌写出来读给老太太听。浓郁的人情味儿,比酒还暖人心。
在一个下雪的日子,我陪一位作曲家手持一支歌子,去了石岛。
其实这是一个寻常的故事,说寻找雪花也可以,因为雪离我们越来越远,在光怪陆离的都市里,人们匆匆喘息着,风呈几何形穿过十字街头,怅惘的黄昏张着血盆大口,吞着五颜六色的欲望。而雪在远处,是一个胆小而羞怯的童年,悄然向这边窥望中学的时候,有一年大雪将这座城市覆盖了,台东一路落了厚厚的一层。
那天上午我们没有上课,每人发一张铁锨或那种竹制的扫帚,与驻守在太平山上的解放军一起,从早晨直到过晌,才把马路上的雪铲干净了,并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堆了高高的断断续续的雪墙。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没有人堆雪人。解放军战士排队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钟了,他们回去食堂里肯定有热饭,而我在那之后,饿着肚子又去粮店门外的雪地里排队买了50斤地瓜。
比我大20岁的作曲家在我那个年龄,背着铺盖卷沿着被大雪覆盖的山道向青岛走来。他口里衔着一支歌,沿曲曲折折的山路走来。据说石岛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写生基地,因为有些渔村保持了原生态的特色,所以学生们每年都来这里写生。包括下雪的时候。
那天作曲家走上海边的渔码头,试图牵起一缕海风作旋律,而码头上的渔女低着头在补网,甚至靠岸的渔船上,舵楼里的男子探出头来,将目光扬撒在她身上,她也依然沉着脸在长长的围中里。北风呼啸着撩拨海面上的白浪,大群海鸥扇动着翅膀,在从船上卸下来的渔箱旁飞来飞去。嘴上叼着香烟的水手,眯着眼睛,将缆绳远远地抛过来,准确地套在系缆桩上,系住了摇摇荡荡的风。补网渔女的手背红得发紫,有的地方结了冻疮。那年我排队买地瓜的时候,两只手冻得没处藏,夹到腋窝里依然生疼,双脚跳动着御寒。有人冻极了,抓起路边的白雪用力搓,然后团成雪球,掷向行人……码头上的渔女在补渔网,雪花便从漫空里飘下来了,那渔女依然低着头,两只手风快地补网。
我们学校门前的甬道堆满了雪,是从操场上堆过来的,操场要用来开会的,必须清扫出来。堆满雪的甬道中间只留了一道巷子,供师生们出出进进。那时候的学生没有打雪仗的,只是那么挤挤挨挨地从雪堆中间走过。
作曲家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门口向里面探头,看里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讲课。说实话,如果他不是站立在讲坛上,在街头的集贸市场上,我肯定会认为他是一个老农民,如果站在码头上,那就是一位已经不能出海的老渔民。作曲家告诉我这是当年与他住在一间宿舍的同学,年龄比他大,到县城读高中的时候,家里已经给他说了媳妇。后来这位同学考进了上海的复旦大学,毕业时学校要他留校教书,他却回来了。
一位1960年代的复旦大学毕业生40多年来,一直在石岛的某中学教书,退休后还被返聘回来辅导毕业班的数学……
大雪果然囤积在黄昏里了,那位同学拍拍手上的粉笔末,走出教室,迎着作曲家,红着脸膛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作曲家接着吟出上两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就像地下党对暗号一样,在我这个年龄,对这种寒暄方式很习惯。
果然在一处整洁的小院里,一位慈祥的老年妇女从温馨的灯光里迎出来,她舒展大方的微笑,给人以雅净亲切之感,在她的目光中传递着一股温暖在你心头,难怪复旦高才生要回来,人的一生怎么才是幸福?更在于那一双巧手,三下五除二,一桌以鱼为主题的海鲜用各种精致的盘子端上来了。雪在窗外瑟瑟地下着,院子里已经厚厚地积了一层。几杯地方白酒下去,情便把持不住了,作曲家是回来寻找他的歌子的,他掏出一张光碟,嘱大嫂打开 DVD机,放出他写的歌给大家听:
小时候,我经常缠着爸爸,看那飘扬的雪花。
除夕夜,爸爸站在阳台上,把洁白的纸片抛洒。
下雪了,雪花飘飘,在台湾的夜空,纷纷扬扬的飘洒,我看见爸爸转过脸去,偷偷地擦着泪花。
我喜欢,纷纷扬扬的雪花,也疼爱亲爱的爸爸。
从此后,这美好的憧憬,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
我知道,我的故乡,在黄河的岸边,那里冬天飘着雪花。
雪花呀,故乡呀,爸爸思念你呀,思念得满头白发。
歌子经当红歌手谭晶的嘴里吐出,在那个雪夜别有一番情味儿。
“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复旦高才生又随口吟来……那个晚上,在白居易的诗意里,我看到了60岁的人的泪花。
我知道那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段情节,更是一个情结——至今没有解开的情结。
我们铲雪的那个冬天,正长身体的我50 斤地瓜没有吃到开春,再到街道“革委会”申请没有获得批准,妈妈急得与管事的人吵了一架也无济于事,瑞雪兆丰年。有一年正月初一,推门见到满地白雪,父亲说今年好年头。可我的心中的雪始终与饥饿和寒冷相连。即使农民,对于瑞雪也是从可以使庄稼借助雪改变土地墒情获得丰收的角度看待的。
人们追寻的现代都市正释放着不尽的能量,在蒸汽滚滚的街道上,在人们情绪灼热的商场里,在红男绿女的酒楼上,雪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词,在鸭绒被的梦里,更难有雪的痕迹了。
韩嘉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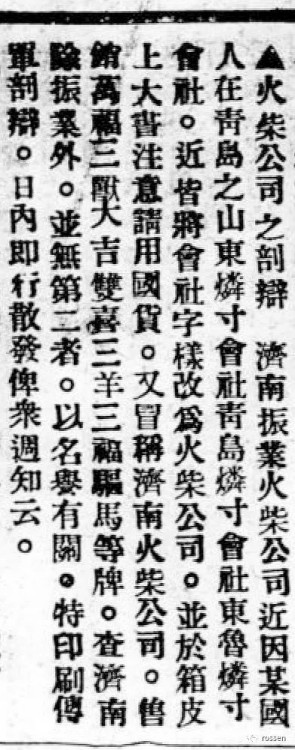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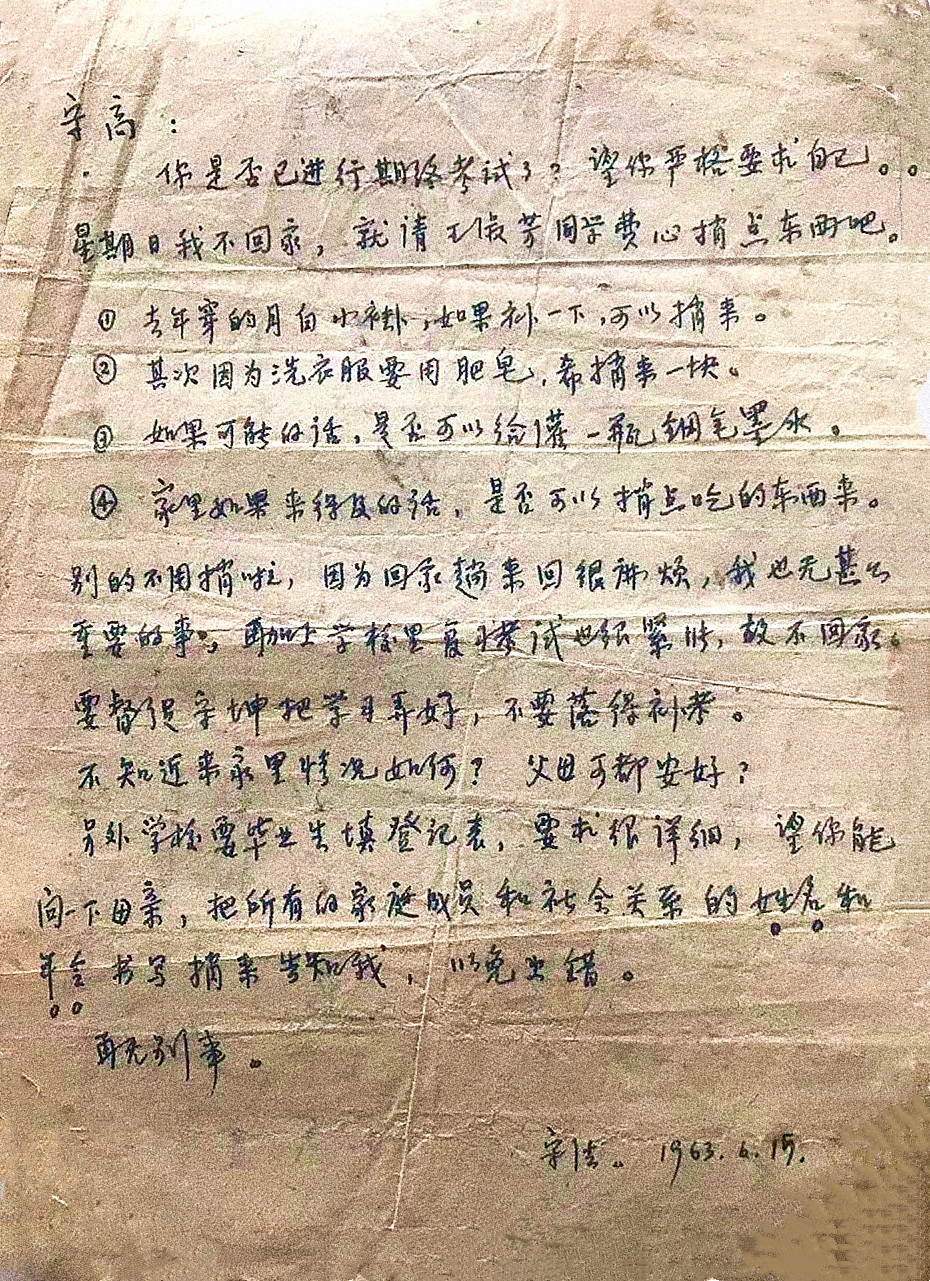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