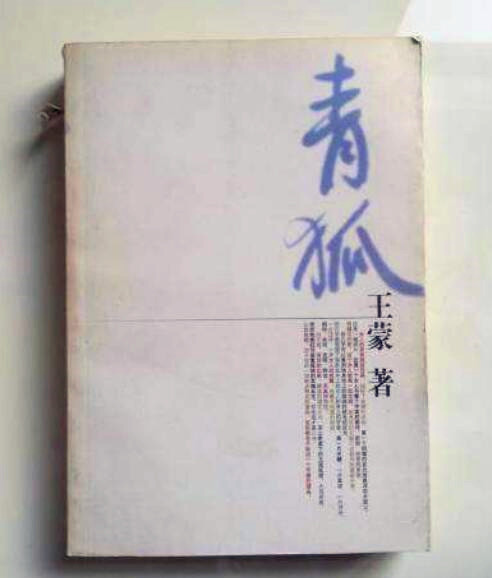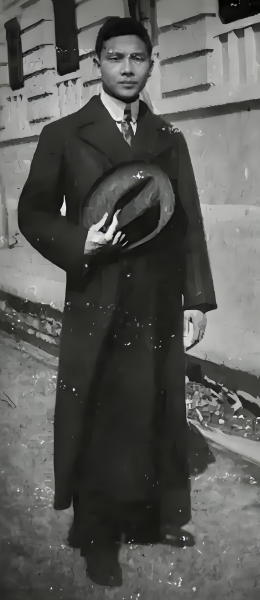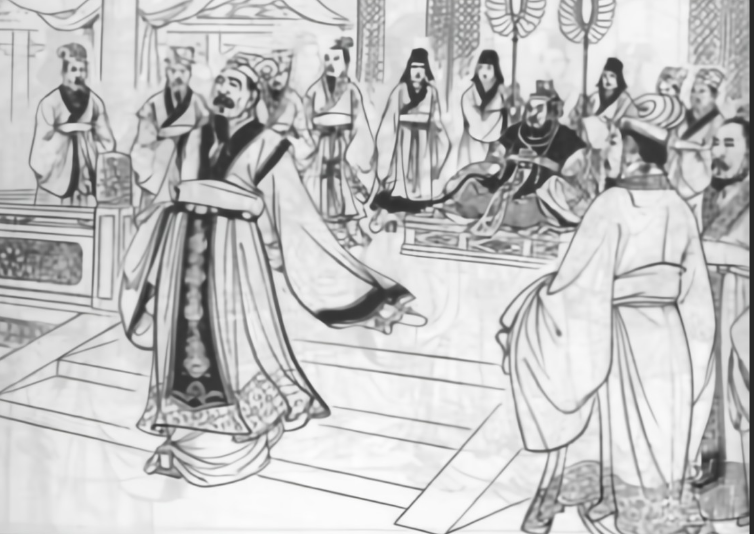读罢《青狐》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说实话,我是抱着一种探究的好奇心去买来一本《青狐》来读的,我想看看王蒙究竟会用怎样的笔触写“性”。这份好奇来源于许多报道,你想,王蒙也以一本《青狐》开始正视“性”,并扬言是“抡圆了写”的、不怕“晚节不保”,这是多大的气魄!更有人干脆把《青狐》的出版与贾平凹的《废都》再版相提并论,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王蒙一向是回避“性”的,他笔下即便写到情爱也多是发乎情止乎礼仪,作为当今活跃着的辈分和职位最高的作家,作为一个历经底层磨难又曾在高位掌旗的作家,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王蒙似乎不“性”,也同样可以叱咤文坛,备受关注与尊敬,怎么老来老去倒用起了不是他自己长项的“性”做自己新著的招牌?
待到我几口气把长达三百多页的《青狐》读完,才发现,王蒙还是那个王蒙。看着书里的插图和他本人的肖像,我突然觉得,他的眼镜后面不大的一双眼睛透着狡黠的光,怎么看怎么像一只老狐狸,我还想起了孔子的话来:随心所欲,不逾距。原来王蒙“抡圆了写”的、不怕“晚节不保”的背后是些与“性”无关的东西,起码不是卫慧或者木子美们的“性”。
一般说来,作品出版以后就不仅仅属于作者自己,而更应该属于读者,每一个阅读者都有权利按自己的理解去读、去品味、去诠释作品,对《青狐》也不例外。作为读者,我觉得自己是有权利用自己的心思解读《青狐》的。
背景
在我心目中《青狐》的最大价值是小说涉及到的时代背景19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从乍暖还寒的1970年代末写起,间或回述思想的暗夜——“文革”时期的荒谬,王蒙用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方式,文学地描述了一个变化的时代里欲退还进的种种事端,这本厚书的最大价值或许就在这里,它几乎可以当成文学领域思想解放的历史来读的。私下以为,王蒙“抡圆了写”的、不怕“晚节不保”的或许就是指的这个。王蒙自己说“在《青狐》中,历史是人性的背景、是欲望的背景、是性格和命运的背景”。
人物
“青狐”——卢倩姑在王蒙创造的众多人物中无疑是一个另类,她的情绪、才气、创作状态、命运变幻都是出人意料而又顺理成章,她对于性的渴望与不得体验的矛盾,她的无意识中的觉醒与时代的不谋而合,她的匪夷所思的创作感觉与进步着的审美需求惊人的一致,她曾经的苦难与尴尬,她的一夜成名,她日渐明朗的判断,她渐入佳境的创作感觉,一切的一切属于她自己更属于她的时代。王蒙是怀着一份怜惜而又审慎的心情刻画这个人物的,这个人物既有合理性同时还包含着冲突。“性”对于青狐是一件奢侈的事,从人物年龄上推论,到接近更年期的时候,她甚至连“性高潮”都很陌生(详见小说之第411页),由此可见,《青狐》一书是作家之意不在性。
钱文——《青狐》中着墨不少于“青狐”的另一位作家,从这位文学功底比“青狐”高出很多、成名特早、聪明勤奋还有不少圆滑的男性作家身上几乎可以看到王蒙自己的影子。书中,即将出任某一领导职位的钱文与另一位作家王模楷又一大段很有意思的对话,几乎就是作家的夫子自道(见小说第394—398页)。
杨巨艇、米其男、雪原等等都会让八十年代的读书人想起一些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中的作家的影子。
至于书中的紫罗兰以及老、小白部长的作为和语言差不多就是那个时期文化领域的真实再现。
语言
有一位小学生的妈妈看了王蒙的作品后说道:可以让孩子看看王蒙的书,词汇太丰富了,本来一个词或一句话可以说明的,他非用一堆词或一串排比。“京油子卫嘴子”,北京作家一般都语言丰富,从老舍到王蒙再到王朔,尽管语言风格存在差异,但用语泼辣,手法新奇,无不体现一种地域特色。王蒙的小说语言特色鲜明,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太主观的语言有时会削弱阅读者的想象空间,王蒙得很多小说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青狐》亦如此。
情节
王蒙可能太讲究小说的“微言大意”,因此,情节就成了他创作的软肋,早就有评论说道:他的小说太冷静,乐于条分缕析地挖掘根源,但却缺少真正的情感投入。如果你看过他的《季节》系列的话,这个感觉就会非常明显。看来,这部被作家自己称为“后季节”的小说还是难以走出业已形成的模式。
总之,《青狐》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关注,值得庆贺的事,对作家和读者同样重要。毕竟王蒙的这部“后季节”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阅读体验。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