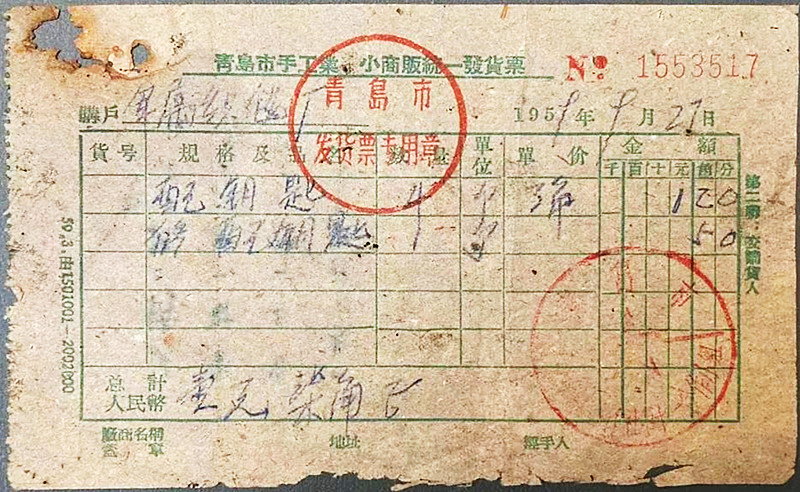接到一家出版社通知,我的一篇散文被收入选本。早期写的作品,贴出来纪念。
好像有人在推我。
“该你站岗了,该你站岗了……”
头颅内像无数尖细的钢针往外迸扎,我睁开发涩滞重的眼睛,梦游一样穿上军装,摸起枕头底下的枪,在满屋高低不一的鼾声中,摸索着走到屋外。
屋外漆黑一片。下岗的战士呆在门口,他低低地说出两个数字,没等我应声,便鱼一样钻到他床上去了。我强迫自己记住那两个数字,那是口令。忘了口令会出事的。
假如你当过几年兵,那你一定会记得站夜岗,一定会和我一样,刻骨铭心地记得站夜岗。
从盖着棉大衣、薄被子的被窝里爬出来,把仅有的一点热气放光,缩着脖子,倚着岗楼冰冷的墙,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岗楼凉渗渗的水泥墙像刀子,透过外衣,刺着你的脊椎骨,直到你的身体发麻、僵硬。下岗后钻回被窝,直到嘀嘀嗒嗒的军号像水洒进油锅里,迸溅起一片起床时的紧张和嘈杂,身子还有些发僵。站夜岗,一小时等于一整夜。
不过,站夜岗使我加深了对大自然的了解。就说天黑的时候吧,那是真黑,黑的让你难以置信:把自己的手指头戳到眼睫毛上,竟一点也看不见;而当月朗风清,你看着自己的影子在沙沙地响,这时候,营区有着特美的意境,排排白杨树高耸在湛蓝的穹窿中,像剪纸一样玲珑剔透,如果是在夏天,你会觉得是走在一幅亮色调的水彩画中。
我服役的部队营房大门前是成片的庄稼地,夏季是一片黑油油的小麦,海一样波动;到了冬天,大地裸露着,沟沟坎坎蓄满了暗影,透出渗人的荒凉来;秋天时是一片过人高的青纱帐,红缨、阔叶和苞米哗啦啦地响,好像,恐怖就是从这时候来的。
常常,我把枪从肩上取下,把银白的刺刀挑上,两手握枪杆,成拼刺刀状。在风声呼啸,月黑冷峭的夜晚,我还违背站岗规定,偷偷地压上两颗子弹,看着黄铜壳、红屁股般的油亮子弹跳进枪瞠,我的心也一下子实落了。那小小的东西真壮胆。
但那站岗的恐惧却怎么也摆脱不掉。
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漆黑的夜晚,附近村庄里的一个企图盗枪者来摸岗,他穿一身黑衣服,手持一把雪亮的锋利斧头,幽灵一样潜到营房大门口。正巧这天站岗的是一个老兵,他很有经验,把雨衣挂在一棵与人差不多高的树上,自己伏在路边的沟里,持枪注视着。盗枪的坏人蹑手蹑脚地摸来,抡起斧头,朝雨衣上的军帽就是狠狠地一斧!“唰”地一声,砍下的不是人头,而是一根雨衣下的树枝。
这个班长听班长的班长讲述的故事,不知传了多少年。这故事使我们站夜岗时毛骨悚然。
一次站夜岗时,我在紧张中听到一阵细微的沙沙声从不远处传来,有人!我不由得头皮发紧,呼吸紧促,手脚竟有些不听使唤起来,沙沙的脚步声更近了,我大喝一声:“站住!我要开枪了!”只听远处“扑通”一声,一个黑影跃墙而过,窜入军营。我同时扳开保险,按动枪机,“叭!”——没有震耳欲聋的枪响,只是撞针击在空洞的枪瞠里的一响,哦,原来我紧张地忘了压子弹。
我咬了咬牙,冒着危险迅速沿着刚才黑影跃入的地方追进去,透过连队厨房门口发黄的灯光,—只大黑狗正惊恐地望着我,又掉转头沙沙地跑掉了。
假如刚才枪真的响了呢?幸好这次忘了装子弹,不然,要编个什么谎言才能遮掩过呢?是不是得朝自己腿上来一枪?然后嚎叫着,把一场违反军纪、酿成大祸的悲剧演成战士斗歹徒?在地上打着滚,最好弄得满头满脸泥土,说是有坏人摸岗,撕打了一阵又跑了。对着因听到枪声围拢来的人,我得像电影上的英雄人物那样,忍着伤痛,奄奄一息地说:“别管我,抓特务要紧……”
站岗长了,很容易使人胡思乱想,尤其是月色普照,大地一片银晃晃的时候,倚在岗楼里,没法关住脑子。
譬如,那一排排部队临时来队家属宿舍的灯光,就好似放射出巨大的诱惑,每每使站岗的人怦然心动。
六连一个老兵,一次站岗时趴在临时来队宿舍的窗户上,窥视难得团聚的一对夫妇的举动,结果被屋里的人发觉了。事情很简单,第二天清晨,这个哨区的连队干部开始追查昨夜谁站几点钟的岗,当吆喝出下半夜一点是谁的岗时,那个叫许黑根的老兵知道赖不掉了,是的,深夜时屋里的人发现窗外有动静,一记住时间,第二天便水落石出。后来徐黑根挨了个处分,直到复员都没抬起头,什么入党、转志愿兵、提干,连想也不敢想了,被牢牢地打发回了农村。嗨,毁了一辈子。
其实,这种半夜趴窗的事每年都有发生,捉着谁谁倒霉罢了。我虽然不曾敢“以身试法”,但对被捕获者倒有一丝隐隐的同情。看着许黑根被人指指划划,脸上由于紧张和压抑而发青发黑,额头上也添了皱纹,我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他从我身边走过,我的脊梁也有些发热,好像在忍受着鄙夷的目光和唾沫。在部队那些年,我真心实意地要求上进(哪像现在这些年玩世不恭),当时我学着别人的样子,跳进粪池里挑大粪,一趟趟地往菜地里跑;牙膏买最便宜的,好像这代表艰苦朴素;袜子破了自己补,一个小洞补二、三个小时;每周日晚上的班务会上,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要向党员学习,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总之,全身心地想抹掉我这个“城市兵”的“城市”印象。奇怪的是,无论我怎么虚心、上进,周围的人好像总同我有些隔阂。
而站夜岗,却把那种隔阂搓碎、揉没了。有一阵连队兴起站夜岗“带岗”,也就是连队干部轮流和战士—块站岗。两个人嘛,起码恐惧感减轻了。
我记得,第一次带我岗的是三排长。我对这个面部粗糙、饭量惊人的壮汉并无好印象,他整天绷着个脸,平时和我连招呼也不打。那次带岗,开始时谁也没说话,只有黑风在呼呼地刮,天昏地暗。我们俩倚着两米多高的墙,挨在一起,不知不觉地聊了起来,话题不知怎么谈到了各自的家庭。三排长说话瓮声瓮气,好像自言自语,说他父亲得了肺气肿,没有钱住院,吃中药把他在部队存下的钱全花光了;媳妇还跟婆婆不和,最近吵着要分家;弟弟偷着上集卖黄瓜,结果给纠察队抓住了,倒贴上了钱不说,在村里的名声也不好听;弟弟快三十的人了,还没凑足钱结婚……
说着说着,三排长直揩鼻子,咳嗽着,骂咧咧地说是风真大,刺眼。我心里好难受,我暗暗内疚,那次我不该当着许多人的面嘲笑三排长挤牙膏太节约,像“苍蝇屎”。
我也说起我的家庭,三排长听了直摇头,说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以前光听说城市人有钱,—天吃好几支冰糕,其实你们也够呛。哎,以后衣服节约着点穿,省下一套半套的给你弟弟。
我直点头,不管他能不能看见。
一夜之间,我跟三排长成了老朋友似的。第二天上早操,虽然谁也没有说话,但彼此对视的眼神大不一样了。
唉,站夜岗,站夜岗……
终于再也不用半夜起来站岗了。而且我还有了自己的床,竟然还有了写字的桌子(在部队除了床下一个抽屉,战士什么用具也没有)。有了台灯,有了垒到天花板的几千册书,有了半夜随便起来读书、写字的权利,有了可以大声发牢骚的自由,有了……在部队时无法想象的许多许多……这使已经转业多年的我,深夜回忆起军营生活,想起站夜岗,一时间心有些激荡,又有些说不出的惆怅。
哦,站夜岗!
杜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