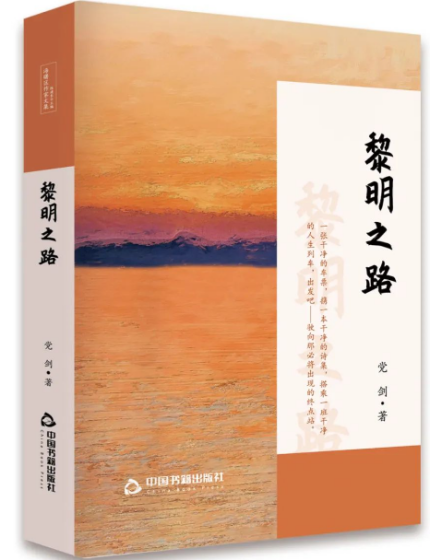这个写诗的原理源于“诗之所以为诗”——“音乐性情调是诗的根本特性”。这个特性只有用民族语言固有的特殊手段,即与体现“诗之所以为诗”的相应形式才能营造出来!
例如汉语写诗的格律。就是汉语写诗相应的表现形式。格律中的五言七言是汉语文字组合中最有节奏感的形式。节奏是旋律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旋律则没有音乐。五言七言含有的节奏感强化了诗的旋律。
平仄音律提供了诗句旋律的元素。即诗的每一个字都是音符。汉语写诗则把这些“音符”按照平仄音律的要求排列,便出现了起伏强弱的变化,呈现出抑扬顿挫的声调,这种声调就是诗的声乐,即诗的“音乐性情调”的主要来源。
尾字押韵则是把每一句诗的声调贯穿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和谐的旋律。于是一首诗的音乐性声调便出来了。诚然,诗的音乐性情调是由诗句的这种源于平仄音律及押韵的声乐与字义共同营造的。也就是说,作为诗的生命的字义,是在与诗句的声乐相得益彰中升华出自身的情调。没有这种“相得益彰的升华” ,字义涵有的情调便大打了折扣。所以古典诗词的“音乐性情调”只有在吟诵中才能体会出来。
对仗是中国古典诗词才有的艺术现象:如果说用五言七言、平仄音律、押韵韵律营造了诗的声乐,从而为诗句的字义锦上添花,出现了“音乐性情调”;那么,对仗则是对这种“音乐性情调”从字义上的“锦上添花”!于是一首严格规范的格律诗,就是这样在格律的层层把关中,完美出了古典诗词才有的那种迷人的“音乐性情调”!格律的这种“层层把关”就是汉语写诗的“戴着镣铐跳舞”的“镣铐”。
所以古典诗词只有吟诵中才能感受到“音乐性情调”的妙如神!这种给人带来无尽精神享受的“妙如神”,是任何其它文学体裁不可能有的。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绝妙所在。
所以离开了格律,这种“妙如神”的情调是不存在的。这是古典诗词所以被誉为世界文学长廊里无与伦比的奇葩的根本原因!
新诗没有格律,即没有营造“音乐性情调”的相应形式。所以新诗虽然可能有情调,但绝无可能有古典诗词借助声乐出现的“妙如神”的情调。
说新诗不是诗,并非是批评新诗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仅是指出新诗没有、也不可能有音乐性的语言声调罢了。没有这种音乐性声调,所谓诗的根本特性“音乐性情调”也就不存在!——这是讨论新诗是否是诗的关键所在!
稍有点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很多新诗自有其文学价值。像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穆丹、艾青、北岛等新诗作者,都有一定成就,其中很多诗句成为民间流传的箴言,有着永久的生命力。谈他们的新诗没有“音乐性情调”是一回事;评价他们的新诗含有的文学价值又是一回事。
“一定的内容需要一定的相应形式予以表达。没有这个相应的形式,则没有了内容;当然,没有内容,形式成了没有意义的空壳”。
——这个看上去人人皆知的哲理,却被不能接受“音乐性情调是诗的根本特性”这个命题的人忘记了!
——格律是汉语诗相应的表现形式,离开了格律这个相应的表现形式,古典诗词那些“妙如神”的音乐性情调也不复存在;如果汉语诗没有那种“妙如神”的音乐性情调的内容,格律便成了废纸一张!
有的人动辄拿《诗经》《楚辞》和李白的古体诗为例,质问: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都不是格律诗,难道能说这些经典不是诗吗?
其实提出“音乐性情调是诗的根本特性”这个命题,仅含有定义(什么是诗)的价值;并非是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这个命题并无贬低《诗经》、《楚辞》、李白的古体诗、新诗文学价值的意思。怎么能说这个命题否定了经典、否定了新诗呢?
提出“音乐性情调是诗的根本特性”这个命题是一回事;讨论《诗经》《楚辞》、李白的古体诗、以及新诗等作品涵有的文学价值是另一回事。将二者混为一谈说事,是否存在语言逻辑上的毛病呢?
有人认为上述讨论,对古典诗词与新诗的定义以及古典诗词与新诗涵有不同的审美价值,有着正本清源的意义。但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发音上,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么,问题就来了:对营造“音乐性情调”至关重要的平仄音律,对今人写旧体诗,是否有意义呢?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但这个问题是另一篇题目的文章了。感兴趣的读者“且听下回分解”吧。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